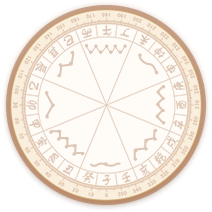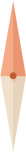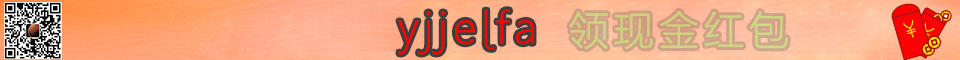

昨晚做了个可怕的梦,梦见我弄丢了儿子······
#男子流浪20年+痛哭说不认识爸爸了#
这两天那可怕的一幕一直在脑海中盘旋:
带俩娃去爬山,因为刚下过雨,原本铺砌的石阶路被水淹没了,要想过去必须要翻越一座小小的山头。危险的是山坡下面就是很陡峭的礁石直通到海里,一不小心就可能滑下去掉进海里。
天下的母亲都一个模样
难得来一次,不能就这么原路返回,那就带孩子们爬过去吧。俩孩子以前以后跟着我,到了最陡峭的地方,我叮嘱身后的大宝不要动,待我将小宝送到上面平台上就回来接他。
好不容易将小宝推到上面平台上,又叮嘱小宝在上面等着妈妈,我去接下面石阶上的大宝。可等我回过头来接大宝时发现孩子不见了,这时候,脑袋一懵变得六神无主,我声嘶力竭地呼唤着大宝的名字,一点儿回应也没有,难道是他自己爬上去了?我爬上平台去找大宝,猛然发现小宝也不见了踪影。
妈妈回来啦
那一瞬间,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的宝贝去哪里了?为什么平时不能对孩子温柔点?如果孩子找不回来我还怎么活?
正在我发疯似地寻找孩子时,一通顽固的电话将我从梦中叫醒。原来是场梦啊,我轻柔地摸了摸还在熟睡的孩子,那一刻,真的感慨万千。谢天谢地只是一场梦而已。以后一定要收敛自己的坏脾气,对孩子态度好一些再好一些。
有了孩子之后,发现自己有了软肋,原本坚强勇敢的自己变怂了,变得不敢穷,不敢病,更不敢死······但更怕的是孩子有丁点儿的闪失,怕自己千辛万苦带大的孩子突然离开自己。
我承认我自己很没出息,只是因为我是个妈妈······
梦见
梦 见
扎好了电车,全友见娘的门关着,心里就咯蹬一下。
门是虚掩着的。
全友推开了门,屋里也没开灯。娘正在床上躺着。
“不得劲儿了,娘?”全友小声地问。
“没啥。”娘边说边撑起了右胳膊,坐了起来。
全友就发现娘的脸有些阴郁。
全友把给娘刚薅的野菜放在餐桌上,娘仍然没说话。
全友的心莫名的沉了起来:娘有想法一向憋在心里,这今天一定是有啥事?
掂了个小板凳,全友坐了下来。
“娘,今儿个天不好,我带你出去转转吧,下午才有雨。”
“不去了,万一下起雨来,一跐一滑的,难受。”
“午饭咋吃的?”
“熬了点米,煮了点豆角。”
“那牙抽空补补吧。”
“我这牙不能补,一补就过敏。上次补了那颗牙,还是从上海回来的医生,只一天,腮帮子就肿了起来。”
“你咋没说?”
“说啥呀,你们都忙。我和你赵姨两个又去找他,把补牙的材料拿掉,第二天就不肿了。”
“他退钱了吗?”
“退啥钱?能给你拿掉就不错了。”
“这补牙的技术又先进了,新材料,应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现象。”
“还补啥,都这把年纪了,不定活个三天两响午的。”
“娘,看你说,还指望你活到一百,抱重孙儿哩。”
“不想啦,况且,今儿个早起又做了一个梦。”
“啥梦?讲讲。”
“不讲了吧。”
“没事,又过了午,讲梦也没事。”
“哎,今儿个早上我梦见你不知是娶媳的还是嫁闺女的,好大一堆人,光花轿就就排多长,那花轿上的花鲜滴滴的,排场得很。”
“那与咱啥关系?”
“你听我讲。我当时就想:这办啥事儿也不能这样铺张浪费啊,回去我就把这事讲给你们听,告诫你们要们俭少。”
“咱家不富,我知道省。”全友笑了。
“不知咋的,这花轿把我抬到了咱老家,一进门,就看见你二叔和二婶在吃饭,还是当年我在家的时候那种粗瓷碗,竹木筷子,碗里是红薯稀饭,大块儿的红薯,黄色的。”
全友的心就莫名的沉了一下:这不是好事。老人梦见抬花轿,暗示你的身体已经很衰弱了,患上严重的疾病,寿命到了尽头,将要与世长辞。
从手机上搜到这些内容之后,全友的脸色就有些不大自然。
“你觉得这梦咋回事?”娘问。
“不咋回事。就醒了?”
“还没醒。我看天快黑了,就对你二叔说,这天都快黑了,我自己一个人又摸不着回家的路,你把我送回去吧。你二叔就说,好,等我把这碗稀饭喝完。他刚说完这句话,我就醒了。”
这抬花轿,鲜花鲜滴滴的,又回到老家,三者一结合,不是啥好事,全友心里合计着。
“你咋看?”娘问。
全友心里一个激凌:“娘,你看今天初五哩,又加上阴天,阴气重,做这样的梦不是啥稀罕事。”
“但我知道你二叔去世了呀。”
“是。但二叔去世也不代表啥。”全友嘴里轻描淡写地说。
其实,全友还有句话没说出来,二婶也已去世了,只不过,这事没敢让娘知道,瞒着她,她和二婶二人的关系特近,前几天还问二婶谁伺候着哩,孩子都是给她买啥吃的。要是她知道二婶也死了,这个打击可不小。
“其实,我不怕死,给个干脆的,两眼一闭就行了,我当年咋着也没想到活到今天这岁数。地震那年,窗户哗啦啦地响,我就想要死了,这么多年,全是赚的。”
“娘,你看现在谁不活个百儿八十的,你才八十,还早着呢。”
“净瞎说,能活一百的有几个?只不过,不火葬,图个全尸,就满足了。”
“大白天的,说这干啥,走吧,到我那住几天。”全友边说边站了起来。
“我不想动,我就觉得我住这儿舒服。”
“娘,你做这梦,可不太好,到我那儿避避吧,就三天,三天成不?”全友不由分说,就卷娘的铺盖。
“唉,我哪儿也不想去。”娘边说边站了起来,“我得把存折带上。还有眼镜、治心脏的药、牙刷、脸盆。这一动就跟搬家一样。”
“咱有车,一车就装完了。”
“我屋里这些东西咋办?”
“这担心丢啊?到处都是监控,谁搬着东西出去那才是大傻瓜。”
“说得也是。”
“娘,快下雨啦,走吧。”收拾好东西,装了车。全友一手攥着娘的手腕,一手去关门。
“别拉我,我自己能走。”
“不行,万一跌倒了我可就成罪人了,弟兄几个哪个会放过我?”全友笑了。
娘也笑了。任由全友抓着她的手,就像她抓着儿时全友的手一样。
消失的女儿:小城里另一个“胡鑫宇”
2022年秋天,整个县城都在传,学校里不见了一个孩子。
失踪男孩叫胡鑫宇,15岁,江西上饶市铅山县致远中学高一学生。2022年10月14日晚17时50分许,他从学校宿舍出去后,消失了。警方、家人、救援队在校内外四处搜寻,抽干了校内水池和化粪池,还启用了搜救犬,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在致远中学门口,徐小琴好几次见到男孩的父母,母亲总是哭倒在地,声音嘶哑,父亲眉头紧皱,沉默不语。
她想到了11年前的自己。2011年5月17日清晨,她13岁的女儿杨紫仪,在铅山县城上学的路上失踪,至今杳无音讯。
徐小琴。本文除特殊标注外,均为受访者供图。
紫仪失踪前两年,徐小琴的丈夫在睡梦中突然去世。寻找女儿,成了她活下去的动力。
这些年,徐小琴跟着寻子家长杜小华,去过北京、山东、福建……2022年起,她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直播,一遍遍举起寻亲海报,讲述女儿的情况:
“她身高1米56,穿37码的鞋,相貌特征是,头发发黄,单眼皮,两个大酒窝,右腿有一块硬币大小的胎记……”
徐小琴不敢细想女儿过着怎样的生活,只求她平安活着。
女儿消失在清晨
紫仪消失后,徐小琴找人给她算命。算命的说,“紫仪人还在。”
11年来,她一次也没有梦到过女儿。也许是好事,她想,女儿没有在梦中向自己求救、喊妈妈,是不是表示她还活得好好的?
紫仪消失在一个清晨。
2011年5月17日早上6点不到,徐小琴像往常一样出门买菜。她在亲戚的公司里干活,帮忙买菜、洗菜、端菜等。出门时,紫仪还在房间睡觉。
等到中午快12点,紫仪没来公司吃饭。徐小琴给她打电话,关机了。她到学校接女儿。老师说紫仪没来学校。她给紫仪奶奶、表姐打电话,都说没见到人。
徐小琴慌了,满大街找。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是不见人。她报了警。
姐姐扶着她,从小吃店、河边、车站找到网吧,找了一整晚,最后走不动了,她瘫在地上哭。
杨紫仪失踪前。
民警后来告诉她,那天紫仪跟同学约好早上去吃烫粉,6点20分左右到了同学家,同学妈妈说,她女儿说今天不是班主任的早课,要晚点去学校,让紫仪先走。大约五六分钟后,另一个女同学给紫仪打电话,让帮忙带包子。过了几分钟,女同学又打给紫仪,电话那端,紫仪声音细细的,说她在做作业,挂了电话。再打过去,电话关机了。
警方最后定位,紫仪消失的地方在同学家附近50米——那里挨着旺子源东路,离紫仪家不过三四百米,隔着两条街,路两旁都是商店。
杨紫仪失踪附近街道。
徐小琴说,那条路上以前很多卖菜卖早餐的,前面不远就是农贸市场,一天到晚都有人,并不偏僻。
十一年过去,这条街道没有太大变化,两侧仍是四层高的楼房,只路口多了两个监控。当年,民警调取了附近农贸市场、超市的监控,没发现什么线索。
2022年2月,徐小琴(中)在姐姐的搀扶下,来到紫仪失踪附近的小巷。
最初,徐小琴以为女儿出去玩了,或是心情不好躲起来了。铅山县城不大,外地人很少。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多年,她从未想过会有人贩子。
电视上登寻人广告,街上贴寻人启事,发传单……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一点线索都没。那段时间,徐小琴每天往刑警大队跑,她眼睛也哭肿了,一下瘦了十几斤。
紫仪的寻人启事。
最后的对话
后来的事,徐小琴很多都不记得了,只清楚地记得,紫仪失踪时身穿灰色薄毛衣,桃红色格子外套,灰色牛仔裤,黄色休闲鞋。
鞋子是新买的。失踪前两天,紫仪说,“妈妈,我这个鞋(穿着)怎么脚趾头那么痛?”
徐小琴俯身按了下,发现女儿的鞋子小了,挤脚。第二天下午,她去买了双新鞋,打折后28块钱,鞋后跟可以翻起也可以放下——天气快热了,这种穿起来透气,她想。
紫仪回房试了下,37码,刚刚好。“妈妈,我明天可以穿吗?”
“可以啊。”
这是母女俩最后的对话。
后来无数个难眠的夜晚,徐小琴总后悔没给女儿买双好点的鞋。
“那个鞋不好穿”,她忍不住想,紫仪万一被人控制了,想要逃跑,那个鞋子容易掉,“她要是没有鞋,那个脚怎么走?”
她不停地设想女儿的遭际:女儿没见过坏人,肯定吓傻了,“我就在(心里)求她,不要倔,要服软,找机会,有饭吃就吃……只要保留体力……”
她怪自己把女儿弄丢了,后悔那天没送她上学。紫仪上小学时,徐小琴和丈夫每天接送,初中她才开始自己上学,晚上补课回来,也有同学顺路。
2022年1月,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为紫仪画的24岁肖像。
这些想法反反复复折磨着她,越想头越痛。凌晨三四点,她一个人趿着拖鞋,到女儿消失的地方游荡。
活着没意思,她想到了死,悄悄囤了十几片安眠药,在一个午后,吞了两片。水洒到地上,她坐地上哭了起来。外甥赶紧把药收走。
“你要这样子,紫仪我们是不替你找的。”母亲开导她,“万一紫仪回来了怎么办?”
是呀,我走了,谁帮我找紫仪?她想,如今自己连死的资格都没有,紫仪要是回来了,自己不在,都没人照顾她,没人给她做饭……
“我要留着这条命。”她告诉自己。她恨拐走紫仪的人,“我要叫他尝受我一样的痛苦……”
痛苦难当,有一次,她抄起红酒往嘴里灌。同事敲家里门,她起身想去开,脚不听使唤,摔倒在地。她慢慢爬到门口,扭开门把手,晕了过去。同事喊来另一个朋友把她抬床上。
那是紫仪失踪后,她第一次睡到天亮。
“日子没有一直这样过下去”
记忆会暂时搁浅,也会在日后反复回荡。
最初的日子,徐小琴总是想起女儿,脑海里像放电影般闪过她的点点滴滴:
生紫仪时,她痛了一整晚,孩子憋得发青才生出来。紫仪刚满月,丈夫开的货车撞上人了,赔了五六万。徐小琴把女儿给母亲带,跑到广东打工,去了不到一个月,挂念女儿,又回来了。
紫仪小时候。
紫仪18个月大时,她就送她上幼儿园,陪她一块玩。小时候的紫仪像个男孩,一头短发黄黄的,眼睛黑黑的圆圆的,像她爸爸。她不爱穿鞋,喜欢在脚上贴贴纸。她总穿纯白的全棉吊带,格子牛仔短裤,“不晓得几可爱”。
大一些后,她跟她爸爸一样内向、话少,她要什么,她爸爸就给她买什么,每天晚上陪她做作业,问她想吃什么夜宵。紫仪有什么都跟爸爸说。她对女儿严一些,紫仪不吃饭、不听话,她会骂她。
那时候,很多人羡慕她有个听话的老公,女儿乖巧,在县城买了房,“生活比别人先走一步”。
她也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直到2009年,生活骤然转向。
那年农历6月19日清晨,徐小琴和丈夫、女儿到庙里拜佛,吃斋面。9点多回去后,丈夫杨冬发说今天要去景德镇出差。他在表哥的公司负责接待工作。
徐小琴自己回了家,女儿去了奶奶家。下午五点多,她给丈夫打电话,没人接。打给老板,老板说,杨冬发没跟他在一起,他上午给杨冬发打过电话,没人接,以为他去休息了。
等到下午六点多,公司保安打来电话,说人在公司三楼。
徐小琴以为丈夫喝醉了,在三楼房间休息。等她赶过去,发现屋里开着空调,丈夫躺床上,嘴唇发黑,咬出一圈印子,手指甲也乌黑。
她唤他名字,没反应,摸他手,冰凉冰凉的。
法医验尸后排除了他杀,具体死亡原因需要尸检。婆婆不忍心儿子被解剖,没同意。
丈夫就这么走了,毫无预兆。徐小琴至今想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在她印象中,丈夫没遗传病,也没生过大病,只去世前一周跟人说过,感觉有些没精神,去打吊针,血管都打不进去。
那段时间,她吃不下睡不下,紫仪也接受不了爸爸的离开。有一次,徐小琴看到女儿哭得很伤心,问她,她说,“别人说我爸爸死掉了,我爸爸才没死。”
紫仪还跟她说,“妈妈,现在没有爸爸了,我们要节省一点,因为你工资不高。”她想买书包,没钱,问表姐借,没跟妈妈开口。
徐小琴心疼女儿的懂事,告诉自己,要振作起来。没想到,两年后,女儿消失了。
紫仪失踪后,徐小琴变得胆小,不敢一个人出门。
年轻时的她不是这样的。她从小没吃过什么苦,父亲在铜矿厂工作,当过村长,母亲在机米厂收钱,家里条件不错。小学毕业后,她觉得母亲重男轻女,赌气不想读初中,在家闲晃了几年,看看西瓜地,拔拔狗尾巴草,15岁到亲戚家饭店打杂。
姐姐们在家排队出嫁。她是九姐弟中第一个出门打工的人。十六七岁时,一个人坐一二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也不害怕。
她去了义乌一家印刷厂,老板娘见她勤快,把她带到广东东莞,让她当主管,底下管着四五十个人。
姐姐、弟妹们跟着她去了印刷厂。一起去的还有紫仪爸爸杨冬发——那是个内向话少的男人,长得帅,爱干净。他们同龄,同村,家挨着,杨冬发为了追求她进了厂。但徐小琴不喜欢他,觉得他幼稚、没主见。在厂里干活时,还差点炒了他。
徐小琴22岁时,母亲叫她回去结婚。来家里说亲的不少,追她的也有,她都不中意。最后想着不如找个熟悉的,她和杨冬发结婚了。
谁会知道后来发生的事。
“在路上,才觉得自己活着”
紫仪消失一个月后,徐小琴买了台电脑,让外甥教她用。
警方调取了紫仪的QQ通讯录。徐小琴从早到晚坐电脑前,加女儿好友们的QQ,跟他们打听紫仪的消息。
有一天,紫仪的QQ突然亮了。徐小琴心怦怦跳,发消息问是不是她,没回复。打视频过去,没接。她马上报了警。
警方定位QQ是在湖南株洲登录的。跟着警察去株洲的路上,徐小琴一直在想,见到女儿要说些什么。
第二天上午,当他们走进那个出租屋,看到登录紫仪QQ号的,是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QQ号是买来的,四毛钱一个,男人交待。
徐小琴只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好失望好失望”。
还有一次,听说铅山河边死了人,她跑去看。一个布袋里传出臭味。她浑身发抖,不敢掀开看。外甥打开后说,“姨,是狗。”她一下瘫在地上。
寻人启事发布后,很多电话打来,有时一天就有七八个。有提供线索的、询问情况的,也有让她充话费的、骗钱的。
50块,100块,她帮人充了好多次话费。有时明知是骗子,也跟人聊;找她视频,她也接。万一别人是真的没钱呢?她总这样想。只是到后来,连骗子的电话都少了。
接到杜小华电话,是在紫仪消失两三个月后。
杜跟她是上饶老乡。他7岁的儿子杜后琪,2011年3月6日在内蒙古包头家门口失踪。杜是电影《亲爱的》四个原型中,唯一没找到孩子的。
徐小琴跟着杜小华一块寻子。
杜小华问她,以后我出去找孩子,你要不要去?
徐小琴开始跟着他跑,“发疯一样”,去了山东淄博、江苏徐州、深圳、福建等地。杜小华走路飞快,她就跟在后面喊,“你要等我哦”。
头几年,她每年出去好几次,近的两三天,远的十来天。有时是帮其他寻子家长撑场子,有时是扩散信息,几十个家长聚集在人多的公园、广场,拿着海报站成一排,“站不住就跪,跪累了站会儿”。有人围观,就问,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宝贝?
夏日太阳毒辣,雨天阴冷。“如果不是孩子丢了,谁愿意出去受苦?”
有一年,她跟几十个家长去北京,大家挤在50块一晚的宾馆,每天一大早出门,拎着包走在凛冽寒风中。等人时,就坐台阶上啃面包、饼干、方便面。
第二次再去北京时,当村长的姐夫、姐姐、弟弟,都劝她回去。
“我说谁都阻止不了我找仪仪,谁阻止,我跟谁拼命,我们就断掉亲戚(关系)。”刚说几句,她就哭得不行,挂了电话。
她知道自己是凑人数的,出不了主意,跑也跑不动。可只有在路上,她才觉得自己是在活着,“我没有放弃”。
徐小琴参加寻亲活动。
其实内心也挣扎,出去次数多了,她愈发觉得,如同大海捞针。“钱用了,人又没找着”。
这些年,她总是没钱。她在丈夫表哥的公司干活,工资才一千多,只够还房贷。出去一趟,远的地方车费就得五六百,再加上住宿费,一年攒的几千块工资,出去一趟就没了。
没钱了,她就找姐姐、老板借,早几年一直欠债,这两年才还清。外甥会帮她买车票,她发工资了再还。
“心里替他开心,眼泪却掉了下来”
和她一起寻亲的家长,有的放弃了,有人有了新的孩子,而她还停在原地。
丈夫去世后,曾有人给徐小琴介绍对象,她想等女儿大点再考虑。后来紫仪失踪了,也不断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她有了更多顾虑:对方有孩子的,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丢了,还有什么心情去照顾别人的孩子呢?也有未婚男人想跟她组建家庭,她拒绝了。紫仪小的时候,她有过一次流产经历,之后无法生育。
她也不愿搬离现在的家,怕哪天紫仪回来了,看不到妈妈。
家里的摆设这些年几乎没有变过。客厅壁龛上,摆放着紫仪的音乐盒、老虎玩偶、彩画。粉色收纳箱里,封存着紫仪的同学录、竖笛、口琴、手套……紫仪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写字台里的东西,徐小琴不敢打开,想等紫仪回来了自己清理。
收纳箱里装着紫仪的旧物。
现在,她常常一个人坐客厅沙发上。以前,紫仪放学了就坐那儿做作业。
她头发大把地掉,记忆力也差了很多,刚发生的事转眼就忘。夜里磨牙、头痛,深夜12点后才能入睡,不到四五个小时又醒了。
在街上碰到留齐刘海的女孩,她想,我的紫仪在哪里?同事的儿子是紫仪的同学,要结婚了,喊她去吃酒席。徐小琴心里替他开心,眼泪却掉了下来。
她不爱去别人家,不爱抱小孩,不敢看现代剧。最难熬的是过年,母亲喊她回去。一大家人聚一起,收压岁钱,吃年饭,独独少了她的紫仪,想到这她的心又揪了起来。
徐小琴把紫仪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等待女儿回来。
她刻意让自己忙起来,每天到公司上班,下班后,在街上走走才回家。晚上,同事、朋友拉她出去散步,跳广场舞。
但心里还是有个黑洞在撕扯她,她变得容易发怒,跟弟弟吵,跟老板急。姐姐们知道她心情不好,都让着她。后来,她不愿意跟别人说起紫仪,连姐姐也不讲,“不想被笑话或同情”。
紫仪刚失踪那些年,徐小琴总想着,等紫仪回来了,她去找个轻松的工作,每天接送女儿上学。
现在,“(被)别人买去做媳妇,我都觉得是奢侈的”,她声音颤抖,眼泪控制不住地往外涌。 “没有吃好的没有穿好的,这些都不重要,只要她能活着能健康”。
“一定要撑住”
2021年12月6日,孙海洋和儿子孙卓认亲那天,徐小琴刷了一天视频,哭到不行,“终于终于有认识的人找到孩子了”。
那年年底,在公益人邓飞和志愿者的帮助下,她的右腿做了股骨头手术——紫仪失踪后没几年,她右腿就开始疼,这三四年越发严重,左脚比右脚长了两公分。
“仪仪你快点回来,妈妈现在已经老了……”面对镜头,她紧握双手祈求。2022年1月,一位在广东手机店工作的志愿者,教会她在抖音发寻子信息,帮她剪辑视频。直播讲到女儿,她总忍不住哭,常被警告、封号。于是,她迅速低下头,擦掉了泪水。
为了寻找女儿,徐小琴开始做直播,总忍不住哭。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徐小琴说,她其实不喜欢直播、发视频,也不爱求人,“为了钱我都不低头”。但为了找女儿,她不得不一遍遍求网友关注,找大号连麦。
2022年年初,央视新闻做了场宝贝回家的直播,很多寻亲家长在上面刷孩子的信息。看到满屏都是别人孩子的名字,徐小琴急得到家庭群大骂,说你们都不管我。大姐、四姐马上给她发语音,说我们弄不来咧,怎么做?只得打电话喊她们的儿子儿媳帮忙发。
当年6月底,她去了湖南、云南好几个认亲现场,小心翼翼地蹭镜头。看到别人找到孩子了,她替他们开心,又有些失落,祈求能接好运。
因为腿受伤,这一年她没有工作,靠杭州花开岭公益机构提供的每月一千元补助生活。她生日那天,有网友送她蛋糕,水果。还有爱心人士,印刷了上万份寻子卡片,张贴在共享单车上。
在昆明的时候,她不知道该怎么买地铁票,两个女孩帮她买,提醒她什么时候下车。她出去找孩子,一些当地网友会去接送。这些善意都在支撑她。
徐小琴(右二)和其他寻亲家长们一起。
2022年7月,警方提取了紫仪爸爸的DNA入库。他们告诉她,现在技术越来越发达,只要监控能捕捉到,就能比对,“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就能回来”。
在杭州做手术时,徐小琴迷迷糊糊地,第一次梦到了女儿。梦中,她对同事说,紫仪回来了,要摆流水席。
真到那天,徐小琴说,她一定要撑住,“不要激动得人晕了过去,不要这么丢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