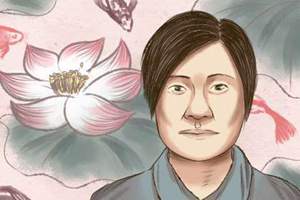青未了 | 李传民专栏:隔屏赏花惹遐思
文|李传民 编辑|燕子 图片|网络
路边上一股北风轻轻掠过,漾起片片锦绣,阵阵花香。摄影快门频频闪过,异彩纷呈,把大自然赐予人间的美丽永远定格在了博友的荧屏上。欣赏着璀璨瑰丽的一幅幅画面,一缕缕绵绵不绝的遐思禁不住纷纷涌上心头。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屋后大奶奶院子里,就有两棵一大一小的花树,由于是无限花序,满树的花朵一年能开多半年,有的凋谢,有的初绽。大家都不知树的科目归属,就叫它花子树,开出的粉红色的花朵就叫做花子。每当阴雨天,院子里雨打花树淅淅沥沥,花瓣上泪珠点点,带着几分忧伤几丝温馨。我常常掐来一束花榾柮泡在瓶子里,天天观察他们的绽放至于枯萎。看过博友的美照,才知道我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花子树就叫木槿树,花子就叫木槿花。我还记得大奶奶常把落地的花瓣拾起来洗净掺上高粱面蒸着吃,蒸熟了就淋上香油给我们送上一两碗。
桃花也是我所最熟悉的,常听人们说谁交了桃花运。大凡人们出生的年月日时称为四柱,每柱都记以天干地支,合称四柱八字。申子辰合水局,阳干壬水沐浴在酉,酉就是申子辰的桃花。凡是年柱地支或日柱地支为申子辰者,其他三柱地支有酉,就是命带桃花,一生男女爱情丰富。人的一生十年一步大运,每步大运各含一对天干地支。假若四柱八字桃花为酉,再遇到地支为酉的大运,就是交了桃花运。十年中进一步遇到地支为酉的年月日时,男女和合自然一帆风顺。那个唐代博陵诗人崔护三顾城南庄茅庐遇淑女绛娘,前两次皆因时运不到而枉顾,崔护题下“桃花依旧笑春风”的千古绝唱于柴门,绛娘也因殉情而身亡。最后交了桃花运,绛娘死而复生,一对恋人终成眷属。自陶渊明写下《桃花源记》,又有历代士大夫把桃花林拟作远离嚣尘的世外仙境。
月季被人们附会成爱情花,还有玫瑰。而蔷薇花是在古诗词散文屡见不鲜的花色。大概多把它喻为平凡低贱的弱势群体吧。只说那樱花,虽说原产于中国,后来移植到东瀛,成了日本的国花。那樱花开得花团锦簇,其风流韵致倒也有几分拖着长裙踏着木履款款轻移的日本少妇风采。但其拥拥挤挤争锋空间的互不相让,又有几分对外扩张的劣根痕迹。
说到荷花,只一篇周敦颐的《爱莲说》,就赋予它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花的名分。从历代文学作品看,贬低荷花的尚不多见。我记得我们家乡古老的县城地处黄河冲积平原,自古就有花城水邑的美称,号称七十二道街,七十二口井,七十二座大水坑。坑坑相连,仲夏时节,荷叶连天碧,荷花映日红。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午后,我们一群孩子光着屁股沿着坑边的泥泞小路,曲径通幽四处漫游,任雨水冲刷。路旁边木槿含露濛细雨,水岸上垂柳依依拂涟漪,雨打荷叶沙沙有声。雨水珠儿随着风动荷叶在上面滚来滚去,像颗颗水银。满池荷花绽放得愈加妩媚娇艳。我逼近荷叶,双手一捧,那凝聚的水银珠子立刻消散,怎么也捧不起来。雨中观荷的景色,整整美了我的一生。
再说那石榴花,每到芒种前后,满树灼灼火红,红得热烈,红得奔放,红得杜鹃声声啼不住。我的初小时代,是在一所没收地主家的厅房里度过的,那院子里就有两棵石榴树。起初是绿树丛中一点红,渐渐地两点,三点,一天天数着吐艳绽放,到了放农忙麦假的时候,满树通红也就数不清了。石榴树下,我的同位英丽天天穿件红裙子打哪里飘来飘去,好像有意和石榴花争奇斗艳。后来我和英丽一起在中心校庆祝“六一”节的大会上代表少先队发过言,声讨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细菌战。直到考上县里的一所中学,我和英丽一直是同班同学,英丽的爸爸就是那所中学的校长。我暗自爱慕英丽,但觉得她是校长的女儿,恨无高枝栖凤凰,就只有暗恋,不敢明宣。英丽对我也是碍于面子有情却没有勇气表达。后来各奔东西而旧情难忘,又互相关注。年逾不惑,终于重逢,互表心迹,悔恨不迭。我于是赠《相思行》一首,开头就是:“石榴开花红胜火,照我幽梦三十春。有情未必终眷属,阴差阳错古到今。”
有博友北风吹者,崇尚自然,奢花成癖。摄有郊外花草精美图片二十余幅,制成博文展示于博客。观后心血来潮,赋《野花》诗一首曰:
春光野外泻丹青,悦目争辉淑气馨。
遍地熔金黄灿灿,一川吐翠绿亭亭。
河边芦苇风飘絮,水上莲荷雨打萍。
喜看风流千种态,堪听婉啭唱黄莺。
有博友戏谑道:“家花不如野花香吗?”我无可回复。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野花更贴近自然,更多一些纯真,它经风雨见世面,多了一些泼辣,少了一些娇贵。如果把它比喻为文艺作品,它是自然谱就的下里巴人,而非宫廷里的阳春白雪。
作者:李传民,笔名雷泽风。男,1945年生,菏泽市人。菏泽市外贸粮油食品公司退休建筑工程师。山东省暨菏泽市诗词学会会员。
壹点号心梦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