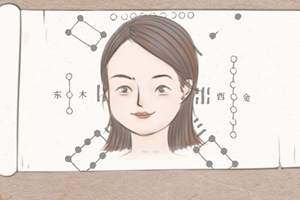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因病去世,自传曾说人生就一个“熬”字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
全文4000字,阅读约需8分钟
据媒体报道,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于9月11日下午3点30分因病在中日友好医院去逝,享年84岁。
单田芳1934年12月17日出生于营口市的一个曲艺世家,是中国评书表演艺术家、作家。2012年,在第七届中国曲艺牡丹奖颁奖典礼上获得终身成就奖。 1954年走上评书舞台。1979年5月1日,单田芳重返书坛。1995年,单田芳成立了北京单田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07年1月26日,单田芳宣布收山,《老店风云》是他的收山之作。2011年,出版了自传《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代表作品有《三侠五义》、《白眉大侠》、《三侠剑》、《童林传》、《隋唐演义》、《乱世枭雄》 、《水浒外传》 等评书。
2010年新京报曾采访过单田芳,原题为《四海为家人生就一个“熬”字》。
惊堂木一拍,白纸扇一抖:“咱们言归正传!” 单田芳76岁,说了55年评书,据说现在全国每天有1.2亿人,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听他说书。人们熟悉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分解了几十年,现在他出了本自传《言归正传》,准备讲讲自己的故事。
故事从哪里讲起呢?伪满洲国、,到新中国,民间艺人颠沛流离,四海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后,单田芳在北京家中缓缓开腔,感慨万千。
━━━━━
少年 乱世求生是学问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我家是世家,从爷爷辈到父辈,都是搞曲艺的,从小我就受这个氛围的熏陶。旧社会艺人没有地位,这是我亲眼目睹的,“下九流”这话外面人说得不多,净是咱们艺人自个儿这么说,确实心酸。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演出都不卖票,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给人敛钱。一段书三分钱,“捧场了捧场了”,就这么喊。人家爱给就给,不给钱也没辙。当时我心里觉着,下不了一个好词:这跟要饭也没啥区别啊,我可不愿干这个。
解放后我也大点儿了,想的是念书考学。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我想当医生,穿个白大褂,戴个听诊器,往屋里一坐,多绅士啊,起码不受风吹日晒。可是赶上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我在东北呆了几十年,现在人说,为什么东北出那么多曲艺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关系?赵本山说原来东北太穷,大冷天人们没什么事干,就互相唠嗑,嘴皮子锻炼得特别利索。这话有道理,也是众多道理之一,我觉得主要还是时势造英雄。东北人本身粗犷,头脑活跃,过去就连做贼都是东北的最多。有句话讲“江北的胡子不开面儿”,知道什么意思吗?“胡子”就是土匪,旧社会太多了,以抢劫为生。你路上遇见胡子了,说是三爷介绍你来的,或者我是谁谁的门下,三老四少给个面儿,该让路的让路,该关照的关照。这都是在西南一带,东北不行。东北的胡子不给面子,管你是三爷还是四爷介绍来的,照样截住打一顿。
所以乱世求生,就是门学问。我那时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领着走江湖,自己不能独立。等到长大了另立家庭,娶了媳妇,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1948年很凶险,解放军包围长春,守军有13万人,连老百姓80多万人困在城里,没水没电,弹尽粮绝。我们家算比较富裕一点,先买下粮食,大缸小坛的都装满埋起来,当时估计这点粮食能维持几个月不断顿。可几个月后呢?谁知道这仗要打多久?最后就是一家人冒险逃出城去,往解放区跑。我现在总结,都是命运,不该你死你就没死。
刚解放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打心眼里高兴。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当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全国解放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毛主席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在革命舞台上表演。后来我才知道,这比打仗厉害多了。打仗时候幸存者还是挺多啊,飞机扔炸弹,哪儿那么巧就扔你头上?可要论危险系数,这个“”是无一幸免,谁都跑不了。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被下放到了农村。
━━━━━
噩梦 四海为家苦漂泊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农村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挣不了三百块钱。光口粮钱就得两百四十块,一年口粮三百六十斤,是毛粮,磨下来就二百多斤成品粮,哪够吃?农村老百姓本地人还有个亲戚能照应,咱是外来户,戴着“帽子”下来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么处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回城里,满腹委屈无处申诉。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就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这样下去,非死在这儿不可。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天罗地网,你能跑到哪里去?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就在外头漂流。哈尔滨、长春、沈阳,好多地方。当时的心情,感觉自己就跟台湾来的特务一样,随时防范人家抓捕。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了制作一种手工艺品,叫“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人家一看,我女儿端个小瓶子站百货商场门口,那花儿五颜六色的挺好看,就都来买。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苞米面一斤三块钱,那也得买,也得活着。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做梦也没想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听说这消息的时候,我还在外边漂着呢,是有朋友告诉我,你那些事儿可以解决了,有说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这词,古书里边有,现如今不可能。朋友说不骗你,给做主了。
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八千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
辉煌 两世为人念故乡
按现在的说法,四十多岁重新开始干事业,不容易。我两世为人,才明白什么叫自由,自由多么可贵。以前说过很多书,看过很多电影,不知道奴隶是啥样。经历一番苦难,噢,原来没落实政策那时候,就是奴隶,变相的奴隶。
我人到中年,对党、对人生充满,感觉像个小孩,一切从头开始。为什么干到今天这么老了不觉得累?就是有奔头,心里头痛快。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随便动弹动弹,说点车轱辘话,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还有俩监听的,还有个主任,录书的时候他们天天在外头坐着,我透过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们当观众,他们也是人,我在里边说,看外边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没把他们说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里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第二个,北京交通越来越不方便,有时候堵车,急死也过不去。我一看,这录音也没什么神秘的,就是墙上贴隔音板,地上铺地毯,麦克买好点的,门加厚点关上,我在家也能录。这样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睡不着啊,工作积压在一起,全国四百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怎么回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这些年下来,要说哪儿是家,真是个难题。如今我人和户口都在北京,公司事业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呗。北京郊区,尤其怀柔那边,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说还出国溜达什么啊,哪儿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岁,也忙不了几年了,心里想着,最后还是得回家。我从鞍山出来,老家熟人多,亲戚多,没事串个门,叙叙旧。北京当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几个人是打伪满洲国那会儿过来的?讲起过去的事儿,还是找东北那些老人。
━━━━━
回眸 言归正传话平生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现在都讲究品牌,电台电视台也一样,放单田芳的评书,听的人多,就有企业愿意拿钱做广告。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的是建国六十年、建党九十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这想法出来,好多人都支持,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给我讲她的经历,讲她的父亲,我很受感动。关于贺龙的书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来,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录了三百集《贺龙全传》。从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直到受“”迫害至死,都录下来了。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现在写出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一百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言归正传,说说自己。从日本人、那年代过来,经历“”、改革开放走到今天,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新京报记者刘臻 编辑 田偲妮 图自视觉中国
值班编辑 吾彦祖
俗话说:“穷灶门,富水缸”,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俗话:“穷灶门,富水缸”,其实它的意思是说:在做饭的灶门口不要放太多的柴禾,而家里的水缸一定要多放些水。可能有人没有太理解,下面我给大家好好讲一下。
1、穷灶门
穷灶门,这里的“穷”,可不是贫穷的穷,而是少的意思。穷灶门就是灶门口要少放一点柴禾,为什么?提醒人们要时刻防范火灾的发生。
要知道,过去的房子大都是土木结构,还有一些干脆就是茅草屋。稍有不慎,就会燃起大火,很快就烧的一干二净。
房不怎么样,但贫穷人家也是要费很大的劲,花不少钱才盖起来的。烧了,就没地方住了,重新陷入困境。
过去用煤很少,人们都用柴禾烧火做饭。一般厨房灶门口的地方经常堆放一些木柴和杂草,方便烧火。但也很大的安全隐患,一不小心,火连火,火连房就会烧起来,造成灾难。
所以,过去人们都会在厨房内贴一张写有“小心火烛”的纸条,目的在于警示烧火做饭的人,注意火烛,柴离灶台远一点,一旦起火,就能起到隔离作用,水火无情,一定不能大意。
2、富水缸
富水缸,过去家家户户都有水缸,一般放在厨房门边,几天就要去井里打水倒进水缸,一缸水吃几天,完了再去挑水。
富水缸,就是说,要经常把水缸放满水,不要等吃干了才去挑水。为什么?这里面很有讲究的,老人们更是讲究,水一少,就赶紧让孩子们挑荷水。
富水缸的原因有四:一是保证家庭不缺水,过去没有自来水,吃水要靠自己去井里挑,有的地方靠天吃水,等没水再去找,就晚了。有的井在很远地方,经常保持水缸满水,这也叫未雨绸缪。
二是人们认为水为财,就是水是代表财富,水越多财就越多,水缸装水就是聚财。三是水缸满水,说明家主人是个会过日子的人,勤快能干,今后一定是过日子的人家。人们到家串门,看见这家小缸满满的水,一定会夸奖这家人是个勤快人。
四是水缸水满,有时也会起大作用,就像前面说的一旦家中起火,又没消防员来灭火,靠谁?靠自己,靠水缸里的水。一发现起火苗头,就近从水缸里用水将火苗扑灾,就会避免大火灾的发生。
不知大家认为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欢迎参加评论。
图片来自网络
散文:水缸
老家有一口最古老的水缸,是用石头打的,我们怀念它的时候,就常常念叨起它的好来,比如:容量大、环保、不容易损毁……儿子在一旁听得仔细。有次,他很遗憾的说可惜我没见过它,我感到吃惊。它是我们那个时代特有的产物,作为隔朝隔代的儿子,没见过也就罢了,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只是后来他的那个认真劲儿,是我没有想到的。
春节回到乡下的老家,他翻箱倒柜地寻找那玩意儿。在他心里,水缸可是个小东西,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安放,好像家里一直给他留着的,专门等他回去看这一眼了。
儿子,你怎么那么执着哟。你以为那是一个玩具水缸啊?
他抓耳挠腮地不知所措。难道玩具水缸不能装水吗?他强词夺理地回击我。
我这才一下子恍然大悟,原来他那么感兴趣、一直念念不忘的原因,是把它想像成玩具水缸了。你那庞大的玩具库里,独缺一个玩具水缸 吗?我问他。
不是这样的。我哪有玩具水缸呀?老爸,你说的那个装水的水缸,我能看看吗?
看倒是可以的,只是它不是我们小时候见到过的那个石头水缸了。
我把他带到水缸前,满满一缸水,黑洞洞的可怕。他把头伸过去看,什么也没发现,只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头影。这有什么好玩的,他索然无味地总结到,随即离开了。
自从在外地工作后,我们一家人就很难在老家团聚。大妹前几年就在老宅的地基上,重新修建了新房。没想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里,竟让我找不到儿时的一星半点影子了。
眼前这个长方形的新水缸,由四块厚度均匀的薄板组成,外围贴上了白色的瓷砖,只有从里面看得出来,是用眼下适用的钢筋混凝土浇灌而成的。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原来水缸的摆设,是在进门的左手边靠墙的位置,离风箱配套的灶台很近。多少次,我挑水回来,都在这熟悉的地形上,左手揭缸盖,右手倒水进缸,再转身离去,一套得心应手的动作,操作起来丝丝入扣。
而现在水缸放到了相反的位置上,如果再如法炮制一回,可能就有撇脚之嫌了;从水缸往锅里舀水,路程远了些,应该也没从前那么方便了吧?!还会洒一些在地上的……水缸与灶后之间,地面上的潮湿,比起以前来就有过之而不及了。
呆呆地想着这些的同时,我在不经意间往地上瞧了一眼,果不其然那里是水帘洞一般的潮湿。
※ ※
当晚,我们就住在用老屋的宅基地重新建盖的新房里,兄弟姊妹们难得凑在一起,把小时候的事聊了个遍,夜已至深,却余兴末了,但身体一次又一次发出的困倦警示,后来实在也忽略不过去了,才索性躺下便睡。
儿子什么时候睡的,我不知道。在我浅浅的睡意中,他既咬牙又梦话,手脚还时不时地动弹一下,梦游般折腾了一夜。
睡的时候,我想过,躺在老家的地界上,说不定会做一个回家的好梦,结果没能入愿。倒是第二天一早,儿子说起了他昨夜所做的梦来。老爸,我昨晚梦见了你说的那种水缸了。
好家伙,居然执着得有些可爱,我在心里说。难怪昨晚那一连串动作,给做的……
一个黑乎乎的大家伙,放在厨房里,像个老古董……我去那里舀水喝了。
这倒有点儿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了。我无声地静待他说下去。
老爸,是不是这样的,你给我讲讲它嘛。
先吃饭,吃完饭后,我带你出去走走,再讲。
早饭后,我们父子俩走在长满庄稼苗儿的田野间。周围的绿色,给我增添了好心情。关于水缸的故事,便这样徐徐展开了。
我们家的水缸是半月型。它的确是个老古董,而且还是个传家宝。常听母亲说起她嫁过来的情景,一个老水缸,每人一个碗,其他就没多少记忆了。婆婆说这个老水缸,是她公公那一代人留下来的。原先很新,也不往外侵水,要足足装下六担水。盖水缸的,是个严丝合缝的木盖。
它最初呈现在我面前的样子,是历经岁月对它的改变而有的老态。鑽子凿过的石纹,已经模糊,它的周身上下,受水的严重侵蚀而潮湿得变黑了。
它就躺在土基墙的一角,底边紧贴墙面,半月的缸沿朝外。竹子编的旧缸盖,随时虚掩在上面。它背后的墙壁上,两根竹纤墙里,托举着槐木扁挑。
为防潮湿,两个木水桶,放在垫着的两块圆石板上。
每次我担完水,都要把水桶、扁挑放回原处,把那有些破损的竹缸盖,平整地盖在缸上。
石缸到底是老态毕现了,就跟老了的人一样,吃进肚里的东西,也不如从前那么多了。每次我挑五担水到进去,就已经接近缸沿了,与婆婆说的要装满六担水的数学有些不符。
这原因,与父亲对它的一次又一次改造有关。水缸的周围,像地下有冒水发了似的,随时总是潮湿的,父亲疑心是缸在漏水。通过检查,也的确如此。便买来珍贵的水泥,在它体力自下而上的糊了一层,尤其缸底是重中之重的糊厚。
这样大致管了几年,缸里糊的水泥起层掉壳,便又重新再糊。
话到这里,忍不住的儿子便问,咋不去买个新的回来用?干吗一定要用石水缸呢?
你说的轻巧,在哪去买?那个年代的农村,如果不用石头缸装水,又能换成什么东西装水呢?
※ ※
我也听到父母亲私下议论过。母亲说要换个新水缸了。你没发现,你用水泥糊水缸,周期在越来越缩短了吗?而且,每次一糊缸,水缸都要凉好几天,才能装水,太不方便了。
我也想换,就是条件不允许。坚持坚持再说吧。
由于平时的耳闻目睹,对家庭的现状我还是知道的,八口之家的我们,仅凭工分,连年补社不说,吃的都是最基本的口粮。无论怎样节约,都还有些青黄不接。凭父亲教书一月二三十元的工资,家庭的开支也时时捉襟见肘。父亲说的条件不允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说真的,换个新水缸的想法,我也有过。挑水基本成了我的事,担回的水随时漏走了不说,就是每次糊缸前后,都是我最无奈的时候。缸要凉干才能糊水泥,糊了水泥后,又要等好几天才能装水。而在这段时间,水屯在两只木桶里,要随时保证有水用,这可苦了我了……
但经过了一件眼见为实的事情后,又让我彻底改变了想法。
我们院子里住着的二爷,他们家几个强劳动力,又有一门编篾货卖钱的手艺,在村里算是有钱的人家了。他们家打了一口水缸,都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结局还不怎么圆满。
那段时间,二爷要我陪他去山上找石料。最后在离家一公里之外的地方找到了一处适合打水缸的石山,但那是在别人管辖的山坡上。好说歹说,别人总算同意开采了,可打着打着石头的硬度又不行了,只有硬着头皮再往下开采。费了很多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帮他给石匠师傅送饭。用整块大石头打出来的水缸,在抬的时候奇重无比,加之下山的路不好走,结果把请来抬缸的人给砸伤了。
※ ※
山风习来,我们坐在一处高地上享受这难得的新鲜空气。我的故事讲完了,儿子半天没说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儿子,怎么了?
老爸,我是不是不该让你讲关于水缸的故事呢?
为什么?
我看到你难过了。我们家以前也太穷了!
正因为以前太穷,过的苦日子太多,我才越发努力去改变命运。
儿子又一次沉默了。他转过身去,偷偷擦试着眼泪,怕被我发现,故意说道,我去问一下大孃,老水缸哪去了。
我在后面跟着,远去传来了吃午饭的叫声。
原创散文,不得侵权!转载请邀约;图片来源于网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