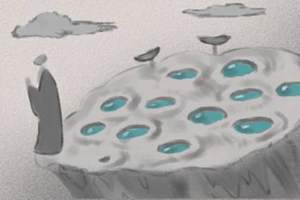第1633章 不想
里长说罢,伸手招来几个孩子,让他们去地里驱蝗虫。 几个孩子便相视一眼,撒腿就往地里跑,哪里草多就跑哪里,呦喝一声跑过去,草里立即扑哧哧的飞出一群蝗虫,在空中飞了一阵避开那几个孩子又落到远处的草丛里。 还有几只蝗虫被赶得急了,慌不择路,直接往他们这群静立不动的人脸上扑…… 里长大惊失色,正想伸手去挡,满宝三个已经眼疾手快的伸手去抓了。 满宝一抓一握,然后捏住还在挣扎的蚂蚱,拎着它的翅膀问,“着还不大呀。” 里长:“……大人,小的说的是蝗灾闹得不是很大,但这些蝗虫还是吃得挺肥的。” 满宝便问,“村里没有养有鸡鸭吗?” 里长愣了一下后道:“养是养有,大人要吃吗?” 满宝捏着蚂蚱笑道:“不是我吃,是这个可以被吃。” 满宝看了看手里的蚂蚱,到底没有捏在手里太久,而是将它丢在地上,一脚踩死了。 白二郎还有些舍不得,捏着他抓到的道:“我记得小时候立重和立威带我们去烤过蚂蚱,也挺香的。” 满宝便低头看着蚂蚱的尸体,略微有些惋惜,“你不早说。” 白善已经扯了一根草将手里的蚂蚱绑起来递给白二郎,指着路上道:“他们也到了。” 里长和村民们被这三个公子小姐弄得有些心悸,他们这样儿让他们有点儿恍惚。 尤其是满宝刚才踩死那只蚂蚱时,总让里长心里有种很怪的感觉。 白善一指,里长和村民们也忍不住扭头看去,就见大路上慢慢来了四五辆马车,他们微微一愣。 马车上的人似乎也看到了他们,在离他们最近的路上停下,然后车上便下来了不少人。 满宝几人迎上去,冲已经兴冲冲走过来的老周头叫了一声“爹”,然后和庄先生、刘老夫人行礼。
刘老夫人微微颔首,举目四望,微笑的问:“这就是你的职田?” 满宝笑着应下,然后和里长介绍,“这些都是家里的长辈,正好我们来附近的庄子里小歇,便顺道过来看一看,这是家父,这是家母。” 里长一愣后立即去和老周头行礼。 老周头对里长也很客气,甚至还有点儿小心翼翼,这是在家里养成的习惯。 老周头看地更仔细,他在地里跺了跺脚,然后就随便找了根棍子挖了点儿土,放在手心里搓了搓,然后看着这满地的野草叹息不已。 他找了找,这一块田应该是种的稻子,他仔细看了看地里的情况,挖了好几个地方都没发现肥,再到旱地上挖了一阵也没发现,便对满宝道:“就这,你还说不自己管,你看看这地都种成什么样了?” 一旁的里长有些尴尬,村民们却有些不忿,张嘴想要说话却被里长瞪了一眼。 白善看到了,便撞了撞满宝,示意她去看。 满宝与他对视一眼,和里长笑道:“太阳大,长辈们不好久晒,还请里长带我们进村歇歇脚,讨一碗水喝。” 里长自然愿意,将来这大片职田都是他管辖之下,而这些职田现在都是周满的,和她搞好关系是必然的。 于是里长躬身请他们进村。
于是一群人浩浩荡荡的进村去,直接去了里长家里歇脚。 里长的儿子和儿媳妇连忙烧水泡茶招呼众人,老周头干脆就拉着里长说起话来,主要说的还是种地的事儿。 那么好的地他们那么种实在是太糟践了。 刘老夫人笑着低头喝茶,钱氏也喝茶,等老周头念叨了一阵才打断他的话,和声问里长他们这里今年的收成如何,几月开始播种,几月可以收获…… “这一地风俗不同一地,我们老家不在此处,也不知道你们这里气候如何。” 今年的收成还不属于周满,是属于上一任官员的,所以里长便是怎么惨怎么说,“周老爷是没看到,之前我们这里的河都断流了,也是今年运气不好,交了定租后,这脚钱还没着落呢。” 正看着屋内摆设的白善回过头来,问道:“脚钱?是丁税的脚钱,还是职田定租的脚钱?” “自然是定租的脚钱了,”里长道:“这些定租是要送到京城去的,由衙门里的大人们来收取,再统一押送进京,这都是需要脚钱的,每一亩地都要一升的米做脚钱。” 白善微微点头,看向满宝,俩人便一起出门去了。
满宝见不少村民都围在里长家的围墙外看热闹,便和白善一起出去,人群立时散开离他们远了点儿。 满宝看了看他们脸上戒备的神色,便伸手进袖子里,从系统空间里摸了一把糖出来,直接找了几个比他们小的大孩子,将糖分给他们吃。 这个糖和刚才分的糖似乎不太一样,刚才没怎么分到糖的孩子们看了一眼大人后便呼啦啦的围了上来。 满宝给白善手里塞了一把,跟出来的白二郎看见了,便冲满宝伸手。 满宝看了他一眼,也给他抓了一把。 白二郎就一边分糖一边嘟囔,“你明明都带糖了,刚才还装作没有,可真够奸诈的。” 白善则是看了一眼满宝的袖子,推了一把白二郎,“废话这么多,我们到一边去。” 白二郎剥了一颗糖塞自己嘴里,然后跟着俩人慢慢往外走,很快就将一群孩子引到了远离大人们的地方。 虽然知道了周满是官儿,但因为她是女孩儿,年纪又小,村里的村民们对他们也没那么高的警惕性了,反倒对屋里的老周头等大人很在意,所以都围在屋外看情况。 三人用糖将村里下至能走的孩子,上至还没成亲的青年都给引来了。 身边围了一大群人,满宝看了眼手上剩下的几颗糖,自己也剥了吃一颗,剩下的就给了两个一看就是才两岁左右的孩子。 然后她好奇的问一个少年,“他们为什么都围着里长家呀。” 少年便看了满宝一眼后道:“你们是贵人,我爹说得去看看明年种谁家的地。” “你们不想种我的地了?” 少年想也不想便回道:“不想。”
故事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离开京沪的人,都去哪儿了?
2018年哪个地方人口流入最多?
北京?上海?深圳?都不是。
记者了解到,近期各个城市开始陆续公布2018年常住人口数据,其中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是广州、西安、成都等省会城市。很多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增长快,但是省内一般的地级市常住人口增长慢。
2018年京沪常住人口为负增长,天津为微弱增长。2018年末广州常住人口增加40多万,2018末杭州常住人口增加33.8万,宁波增加19.7万,南京增加10.12万。郑州和西安的数据将发布,根据公开数据推算,2018年末两地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10多万和40多万。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指出,一些超大城市生活压力较大加上产业结构变化,常住人口可能会转到其他城市,所以这些城市有了发展机会。广州、深圳的制造业产业发达,对人才吸引力大。
近期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一次论坛上指出,通过城市人口的收货地址大数据看,从北京迁出的人,首要迁出目的地是天津、廊坊、深圳、广州,而从上海迁出的人口,则偏向去往邻近的苏州和杭州等,显示新的城市集群已经开始形成。
京沪迁出人口流向何方
各地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末上海、北京、天津常住人口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1.37万、2.2万、5.25万。扣除自然增长因素(出生人口数减去死亡人口数),三地净流出人口数量分别为8.2万、10.4万、9.28万,合计27.88万。
2018年,这一趋势仍然持续。2018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2154.2万人,比上一年减少16.5万;上海常住人口为2415.27万人,比上年减少3万以上;天津常住人口总量1559.60万人,比上年增加2.73万人,增长0.2%。
丁金宏指出,上海、北京此前人口净流入过多,现在回流是正常的,人口是否流出到周边地区,需要看周边地区的产业能否提供就业机会。
河北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河北常住人口仍属于净流出状态(常住人口新增数小于常住人口自然增长数)。这也表明,尽管北京常住人口负增长,但是北京流出的常住人口并未大规模流向河北。
上海周边的杭州、苏州、南京、宁波、湖州、芜湖等城市,2018年常住人口处于正增长状态,且净流入比较多。
浙江人口抽样公报显示,浙江2018年末常住人口净流入49.01万,其中杭州净流入27.83万,宁波净流入15.81万,嘉兴净流入4.28万,而台州、丽水人口是净流出状态。
安徽人口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末合肥常住人口净流入5.15万,芜湖净流入3.18万,马鞍山净流入2.19万,但是宿州、蚌埠的常住人口为净流出状态。
近期京东的一份报告指出,2018年前9个月迁出人口比较多的城市主要在一线二线。许多一线城市迁出的人口主要去往二线、三线以及四线城市。其中,北京迁出的人口多流向天津、廊坊、深圳、广州,上海迁出的人口去北京、苏州、杭州、深圳较多,广州迁出的人口去佛山、深圳、东莞较多,深圳迁出的到东莞、广州、惠州较多。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王金营教授指出,北京、上海常住人口下降,主要是人口疏解的结果,未来产业结构调整好了,再加上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可能常住人口还会增长。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各地人才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尤其在人口不增长或者负增长的时候,这种激烈的人才竞争也是一种外力,驱使人口流动,由此导致了不同地区人口的变化。”王金营说。
为何省会常住人口增长快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省会城市对本地区的常住人口吸引力较大。很多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在当地增长最快,这在一些热点城市表现明显。
各地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末,广州市常住人口1490.44万人,比上一年的1449.84万数字增加了40.6万;成都市常住人口1633万人,增加28.53万;杭州常住人口增加33.8万,达到980.6万;合肥常住人口增加12.2万,达到808.7万。
深圳、郑州、西安尽管没有公开发布具体的数字,但是很多相关数据表明,这些地区常住人口在快速增加。
深圳市两会期间公布的报告指出,2018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4万亿元,增长7.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19万元。按此测算,2018年深圳常住人口是1274万,比上一年的1252.83万,约增加了20万。
西安和郑州2018年常住人口过千万消息已经发布,按此看2018年末两地常住人口将分别增加40多万、10多万。
中山大学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袁持平指出,一些热点城市占据国家战略要地,比如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这些城市发展得快是正常的。同时,武汉、成都、西安也出台了很多吸引人才的政策,对年轻人吸引力大。
“很多地方高科技产业发展快,这对年轻人最有吸引力,一些初创公司加快孵化,有利于促进产业发展和人口增长。”袁持平说。
数据显示,很多热点城市常住人口增加快,其不二法宝是吸引大学生落户。
根据西安市发布的消息,截至2018年12月31日,西安新增落户人口超过105万,户籍人口共计9923159人,将突破1000万。根据2019年西安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全年西安落户人口80万,引进培养各类人才38.6万人。
此外,成都2018年末户籍人口1476.05万人,增加40.72万人。武汉2018年末户籍总人口883.73万人,比上年增加30.08万人。广州2018年户籍迁入人口22.81万,高于2017年迁入18.06万数字。
很多省会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在当地是一枝独秀,比如贵阳2018年末常住人口达到488.19万,增加7.99万,相当于全省常住人口新增量20万的1/3以上,而第二名毕节2018年末常住人口增加量只有2.64万。
西安2018年常住人口增加了40多万,而陕西全省2018年末才增加了28.96万。省会城市常住人口增加量为什么比全省的还多?这是因为陕西一般地级市人口增长慢,大量本省人口涌入到了省会城市。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所教授姜全保指出,京沪最近多年采取严格的人口调控政策,所以人口减少了,未来城市群之间各个城市会发生互动作用。上海将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而河北要快速发展经济才能吸引北京流出的常住人口。
珠三角、长三角整体常住人口增加快,与这些地方的一些优势有关,比如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收入水平高、气候温暖、落户门槛相对不高等。
“哪个地方经济搞得好,人才政策好,就对人口有吸引力,人们会选择用脚投票。”姜全保说。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西班牙和葡萄牙争夺远东保教权的第二阶段是什么样的?
前言1580年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后,双方的斗争随即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斗争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即“两国的亚洲保教权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为菲律宾的托钵修与澳门的耶稣会士之间的斗争了”中国、日本成为了双方斗争的焦点。
对中国传教权的争夺16世纪下半叶,当耶稣会士为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而精心准备时,西班牙的托钵修会也在为这事忙碌着。正如意大利学者柯毅霖所说:“耶稣会不是唯一有去中国之计划的修会。另外三个修会,即奥斯定会、方济会和道明会也定居马尼拉,目的是进入中国。”
而明清之际,“通过菲律宾来中国传教的托钵修会主要是方济会、道明会和奥斯丁会,他们基本上是由清一色的西班牙传教士所组成。”西班牙托钵修会突破葡萄牙远东保教权进入中国内地(相对于葡占澳门而言)传教的努力可以1633 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进入福建传教为分水岭,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从16 世纪70年代到1633年为前期该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西班牙传教士以菲律宾为基地,以台湾为踏板准备向中国内地渗透。方济各会到达菲律宾后,急于开教中国,先后于 1579、1582和1587 年做了三次前往中国传教的尝试,但都以失败结束。
多明我会于1587 年在澳门建立了玫瑰圣母会院(Santa Maria de Rosario),这是该会在中国所建的第一座会院,也是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但最终被耶稣会强行占有。另据史料记载在1590到1619 年间,多明我会士曾八次尝试从马尼拉前往中国。
不难看出,这些西班牙托钵修士在立足于菲律宾之后都非常急迫地向中国内地进军,但又都遭到了失败。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明朝的海禁政策,然而更重要的还是由于澳门葡萄牙当局和耶稣会的阻挠与暗中破坏。
“他们害怕西班牙人的到来会扰乱他们已经同广州建立起来的定期贸易往来。所以葡萄牙人散布西班牙传教士是“间’以及他们身后有一支舰队要来占领中国’等不实之词,目的是要引起的关注,将他们驱逐出境”。
耶稣会则害怕在中国出现一个与之相竞争的西班牙托钵修会,从而将打破它断中国内地教务的局面。当西班牙籍方济各会利安当神父 1633 年前往南京时,“他在江西省的建昌、南昌和南京不仅没有受到耶稣会神父们的欢迎,最后还被南京的徒们捆了起来送上船,押送回福建。”
1585年,在耶会远东视察员范礼安的强烈请求下,教廷更是宣布禁止耶稣会以外的其他修会进入日本和中国。对于西班牙托钵修会来说,这意味着它们被剥夺了对华传教的权力。这也是一心想通过传教发展对华贸易的西班牙所无法容忍的。
菲力普二世向罗马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和抗议。教廷迫于压力,同时也对葡萄牙垄断远东教务后那种桀警不逊的态度不满,就在 1608 年宣布托钵修前往远东可自由选择路线,不必经里斯本,1633年教廷又宣布一切修会和宗教团体都可任意选择路线前往远东。
这表明西班牙传教士从“教理”上彻底摆脱了葡萄牙保教权对他们前往远东传教的种种限制。他们接下来所要解决的就是选择前往中国的具体路线问题了。最终他们把目光抛向了台湾岛,企图建立一条马尼拉一一台湾一一福建的海上传教航线。
而其实早在1619 年西班牙籍多明我会士马涅(Bartolome Martinez)就曾对台湾岛沿岸进行了勘测和绘制地形图,并向菲律宾总督建议在台湾建立据点。早已迫不及待的西班牙人于 1626 年攻占鸡笼和淡水,而随军前来的多明我会士则在台湾开展了传教活动,建立了一所住院和一座教堂。
这为1632 年多明我会士高奇 (Angel Cocchi)顺利潜入福建传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奇在福安县扎下了根,建立了多明我会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座教堂,该会在中国的正式教区也随之成立。
1633年多明我会士黎玉范(Juan Bautista de Morales)神父和方济各会士利安当(Antonio de Santa Maria Caballero)神父从菲律宾经台湾前往福建传教。这标志着西班牙托钵修会对华传教事业进入了第二个历史时期,即取得实质性成果时期。
西班牙在华的教会势力也日益壮大,尤其是方济各会。利安当在 1650 年毅然北上山东,“在济南建立了方济各会在中国的第一座教堂,该教堂于 1651年8 月正式祝启用,标志着方济各会中国教区的正式建成。”
文度辣神父(Buenaventura Ibanez)则成功“说服了西班牙王太后,由王室负责向方济各会中国传教团提供固定的拨款,为期 5年,而且年限可延长。”尽管王室的经费经常会拖欠,但这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他们在中国传教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为他们在中国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财力基础。
此后,他又于 1679年建成了方济各会在华的第一座西式教堂一-“杨仁里福音堂”,这“标志着方济各会已经在广州扎下了根基,广州开始成为方济各会在中国传教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在西属菲律宾总督的支持下,方济各会通过与耶稣会协商,迫使其答应由前者负责粤东的教务。
据此协议,方济各会先后在东莞、惠州、潮州和顺德建立了教堂,设立了传教区。另一位入华方济各传教士利安定神父 (Augustinusa S.Paschale)在1672年到达广州后,先后恢复了方济各会福建、山东教区,开拓了新的江西教区。至此,方济各会在中国形成了以广州为总部,拥有广东、山东、福建和浙江四大教区的新局面。西班牙传教士在华影响不断增大。
对日本传教权的争夺对在远东立足的传教团来说,到中国传教是他们传教使命的最高荣誉,日本则是他们的一个热门传教目标。尽管日本被葡萄牙包括在了其远东保教区内,来自澳门的葡系耶稣会士也已经在日本进行了长时间的传教活动,但来自菲律宾的西班牙传教士还是把日本当作了他们在远东地区传教的首选目标。
1584 年5名西班牙方济各会士抵达日本平户。他们敏锐地发现了当地领主和葡萄牙传教士、商人的不和。
通过交涉,该领主发出了对西班牙传教士和商人的邀请,西班牙教会势力正式在日本登陆。1587 年,因遭丰臣秀吉的驱逐,葡系耶稣会士被迫停止了活动,而西班牙方济各会则乘机展开传教活动,几乎占据了过去耶稣会在日本的地盘。
西班牙托钵修会的这种越权行为,受到了西班牙王室的支持。西班牙一直把对日本的经济和宗教渗透作为扩大其在日影响的一个重要步骤,希望能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过日本的对外贸易,并把它转移到马尼拉的控制下。
西班牙国王菲力普二世在1588 年就日本主教区的设立及其保教权一事给教去信,说其“欲仿效其前任葡萄牙和阿尔加维历代国王之模范”表示自己不打算信守与葡萄牙人达成的君子协定,并对这一新主教区的保教权具有“极大的热情”,欲将它转入西班牙势力范围之内。
面对前文提及的教皇 1585 年对远东西班牙托钵修会的禁令,菲力普二世更是向菲律宾的王室司法行政院下令,声称教皇的敕令没有经过西班牙枢机会议的批准,不得在远东实施。1593 年 5 月,在马尼拉的西班方济会们议定罗马教的令对他们没有影响。
1592-1594 间,有三批方济各传教团从菲律宾前往了日本。1600年德川家康任命方济各会士吉色斯 (Jeronimo de Jesus)为使节前往菲律宾,以打开日西贸易关系。而随着马尼拉与日本贸易的兴隆,西班牙教会势力更为发展。
方济各会重新被准许在日本传教,并在大板坂、京都和长崎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多明我会和奥斯丁会也于1602年抵达日本,开始了在日本的传教活动。他们拒不承认葡萄牙和耶稣会的传教特权,也不承认日本主教(耶稣会士)的权威与管辖,甚至还公开挑衅,要将日本主教置于马尼拉大主教管辖之下。
掀翻“海上马车夫”:1633年中国海商的料罗湾大捷
17世纪上半叶正是荷兰历史上“黄金时期如日中天的正午”。荷兰商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几乎垄断了欧洲的海上贸易。“荷兰人从各国采蜜……挪威是他们的森林,莱茵河两岸是他们的葡萄牙,爱尔兰是他们的牧场,普鲁士、波兰是他们的谷仓,印度和阿拉伯是他们的果园”。荷兰方面的材料则记载荷兰人侵扰福建漳州时,焚烧中国帆船六七十艘,并抢劫、焚毁了许多村庄。此后,他们在福建沿海不断地抢劫福建商人的船只,掳卖中国人,人数达1400名之多。
福建商人集团面临荷兰殖民者的欺压,却很难得到来自明朝政府的支持。1625年4月,当荷兰人与福建官府谈判澎湖群岛问题的时候,悄悄地派出舰队去马尼拉海面抢劫福建商船。他们很担心这种做法得罪福建官府,所以,他们向一些亲荷的福建商人咨询,荷兰档案中有如下记载:“因问该Wangsan以该戎克船中之数艘,如被我方船舶捕获,则军门对此将有何说?据言当不发生任何问题,不过为遭遇此劫者之不幸耳。……又言军门及都督任职仅三年,故不欲与中国治外之人惹起争端,一切尽量避免,盖此举并不受国王之感谢,且无所收益”。明代官府对海疆民众利益的漠不关心,连海外国家也看得心寒。
因此,福建海商只有靠自己的奋斗来解决问题。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在把朝廷前来“清剿”的福建水师打得又一次“官兵船器,俱化为乌有”之后,郑芝龙正式接受了明朝廷的招抚,就任五虎游击将军,坐镇闽海。此时,他所拥有的海船竟然多达1000艘,部众三万余人。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们一样,接受招安后的郑芝龙的任务就是清剿他过去的同行,几年之内,他相继消灭李魁奇、杨禄杨策兄弟、诸采老、钟斌等海上势力,随后,已经成为明朝官军的郑芝龙部众,与荷兰殖民者展开正面对决——胜利者将成为中国海的掌控者。
崇祯六年初(1633年),窃据台湾的荷兰殖民者荷继续推行强买强卖、进而大规模袭掠的海盗政策。1633年7月,8艘荷兰战舰乘明军毫无戒备之机,以突袭手段,向厦门港内的30艘福建水师战船进行炮击。这些中国战船是郑芝龙仿照荷兰战舰模式建造的,舰体庞大,装备精良,船上还装备了一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上的红夷大炮。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25艘中国战船被摧毁,死伤官兵数百名,厦门港亦被荷兰军舰封锁。
郑芝龙立即做出反应,集中了150艘战船,其中有50艘大型帆船,向封锁厦门的荷兰军舰发动进攻。荷兰人被驱离了厦门湾,郑芝龙乘胜追击。九月二十日(1633年10月22日),在金门料罗湾,郑芝龙将50艘郑氏战船分成两支分舰队,其中一支舰队在下风处迂回包抄荷兰舰队(9艘战舰)退路,另一支分舰队则在上风头向荷兰战船直冲过来。当更近一些的时候,郑芝龙命令将福建水师的100艘小船点着火,向荷兰人发动火攻。郑芝龙的战船、火船乘东北风向九艘荷舰冲击,炮火硝烟将宁静的港湾烧成沸腾的地狱。恐怖难以想象。据一位荷兰目击者描述:“有三艘战船包围了Brouckerhaven号,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我们的枪炮和火焰。荷舰尾部起火,火药库爆炸,立即下沉。又一艘荷舰正在近岸处,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
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在东方海域的暴徒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灾难降临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他们的眼里,灰蒙蒙、怪石嶙峋的中国海岸,只有好看热闹的百姓、索贿撒谎的官员与懦弱无能的士兵。而在这个早晨,一切都变了。明朝(郑芝龙)水军的英勇令他们吃惊。三艘夹板船被焚毁,一艘被俘,84名荷兰人被生擒,另有许多死伤。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大捷,正好为郑和远航突然中止献上了最好的200周年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