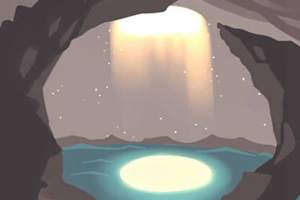看着有福,文殊菩萨精美圣像集
文殊是一切如来之智慧,又名智慧佛。因德才超群,居菩萨之首,故称法王子。
文殊菩萨的名字意译为“妙吉祥”,是佛教四大菩萨之一。
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左胁侍菩萨。
文殊菩萨是聪明智慧的象征。德才超群,居菩萨之首。
文殊菩萨亦常乘坐狮子座骑,表示智慧威猛无比。
在《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称文殊菩萨为“三世佛母”-三世诸佛成道之母,因而有“三世觉母妙吉祥”的尊号。
常见的文殊像,顶有五髻,表示五智无上无得之相。
文殊菩萨与佛陀、普贤菩萨合称华严三圣。
文殊或曼殊,意为美妙、雅致、可爱。
师利或室利,意为吉祥、美观、庄严。
文殊菩萨的形象,通常是右手持慧剑。
左手持的莲花上放置「般若经」。
或驾乘金色孔雀,比喻飞扬自在。
文殊菩萨教导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苦,一切贪爱的心都要没有。
传说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演教和居住的地方,文殊菩萨会接每个前往的人。
持诵文殊五字咒,据佛经记载为:罪障消灭,获无尽辩才,所求世间,出世间事悉得成就,令众生智慧成就。
文殊菩萨心咒:嗡ong 阿a 喇la 巴ba 札zha 那na 谛di
张雅静:汉传佛教文殊菩萨图像的中国化及其流变
文殊菩萨是佛教中重要的尊神之一,在早期大乘经典《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法华经》当中,文殊菩萨以“文殊师利法王子”之名出现,后来成为菩萨当中的重要一员。在大乘佛经中,文殊菩萨是诸佛智慧的象征,为诸菩萨中的上首,在经典中常为机敏善辩的说法者。文殊之名来自梵文名称Mañjuśrī,音译作文殊师利、曼殊室利,或意译作妙音、妙吉祥等。佛教美术中的观音象征着慈悲,通常以柔和慈祥的样貌示人,而文殊象征智慧,通常以勇猛无畏的童子或少年之形象出现。尽管文殊在佛经中是智慧之象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但佛教经典中出现文殊形象的描述,以及印度佛教美术中出现文殊形象的时间却并不早。汉译佛经中关于文殊形象的文字描述,主要集中于唐代翻译的密教经典,大多为童子形,左手持优钵罗花,身色多为金黄色,有些经典还提到文殊骑乘狮子。笔者曾经撰文分析过印度文殊像之特征与演变。大乘佛教中较为重要的菩萨,例如观音和弥勒,在公元2世纪前后的犍陀罗和马土腊造像中已经颇为流行,但印度现存确定为文殊菩萨的造像,最早见于埃罗拉石窟。其中的文殊菩萨制作于9世纪前后,或单独出现,或作为八大菩萨的一员。印度的文殊像或坐或立,姿态众多,尤其在波罗时期,发展出众多具有密教色彩的形象。宝剑与经书,以及优钵罗花,都是印度文殊像手中常见的持物。从图像学特征考察,印度的文殊像,被认为受到了印度教迦希吉夜(Kārttikeya)像的影响,迦希吉夜为湿婆神之子,是一位英勇善战的少年,以孔雀为坐骑。菩提流志译《佛说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载:“若入阵时画文殊师利童子像及真言,于象马上置安,军前先引,诸军贼等不能为害自然退散。其画像作童子相貌,乘骑金色孔雀。诸贼见者悉皆退散。”这段文字中所说骑乘孔雀,且能够击退敌军的文殊童子像,从图像特征及功用上都能看到迦希吉夜的影子。尽管汉传佛教美术中的许多尊神形象来源于印度,但文殊却是个特例。从现存实际作品来看,汉传佛教美术中出现文殊像要远远早于印度,并且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强烈的中国化特色,在印度的文殊像形成和传入之后,又出现二者的并存与融合,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关于汉传佛教美术中的文殊菩萨,许多学者都曾进行过详细研究,孙晓岗先生的《文殊菩萨图像学研究》一书中,对文殊菩萨图像的发展和变迁进行了总结,此书着重梳理了唐代及之后的文殊图像系统。潘亮文女士在《北朝时期的维摩诘经美术研究——以单体造像作品为中心》一文中,对北朝单体造像中的维摩诘经美术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归纳和总结。另有对于五台山文殊像,以及华严三圣等图像进行探讨的诸多文章与论著,不一一列举。本文并非针对某个时代或某种特征文殊像进行的探讨和研究,而是从大的发展脉络上,总结汉传佛教文殊图像的演变和特点,从而揭示文殊图像在佛教美术发展中所具有的特殊进程。一、北朝时期的汉传佛教文殊像关于汉传佛教中的文殊像,许多相关论著提到《法苑珠林》中的记载,东晋陶侃任广州刺史时,渔人从海中得阿育王造文殊像,陶侃将其供奉于武昌寒溪寺,后移江洲,安置于东林寺。《历代名画记》卷三载甘露寺保存的作品中,称有顾恺之画维摩诘与戴安道所绘文殊,均位于大殿外西壁。“宋元嘉二年(425)刘式之造文殊金像朝夕礼拜”。这些文献中提到的“文殊像”样貌我们不得而知,但说明汉传佛教对于文殊像的关注似乎由来已久。从现存实物来看,汉地文殊菩萨形象的出现,伴随着《维摩诘经》的流行。《维摩诘经》在印度大约形成于公元1—2世纪,以维摩诘和文殊等诸菩萨和比丘的对话,阐扬大乘般若性空的思想,尤其受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欢迎。此经于后秦弘始八年(406)在长安译出,但据《开元释教录》之记述,此经在中国早有流传,多次被翻译成汉文,可见其受欢迎之程度。伴随着《维摩诘经》的流行,维摩诘与文殊对坐说法之形象,也开始出现在汉地的佛教美术作品中。现存最早的汉传佛教文殊像为公元5世纪的作品,这时的印度尚未出现文殊像,当时的佛经当中也没有对于文殊样貌的记载。由此可以想见,文殊在汉传佛教美术中出现之时,是没有印度图像可供参考的,因此汉地早期的文殊形象,纯粹是中国人依据佛经对于文殊的想象和表达,这一形象从图像的角度来说,除了借鉴当时从印度传来的其他菩萨装束,并无太多可供参考的图像资料。这一点,从文殊像一开始所具有的中国化特征能够得到印证。维摩诘与文殊对坐说法之题材,除了出现于石窟造像中,也常见于各种单体佛教造像。根据潘亮文女士的统计,北朝单体造像中出现此题材者以河南为最,共有22件,另有河北2件、陕西5件、甘肃5件、山西6件、山东4件、安徽与成都各1件,地域不明的作品共7件。文殊与维摩诘对坐说法题材之流行,由此可见一斑。现存佛教美术作品中,最早表现《维摩诘经》之题材者,见于炳灵寺石窟第169窟北壁,此石窟开凿于西秦建弘元年(420),现存维摩诘像两处,一处榜题“维摩诘之像、侍者之像”,维摩诘菩萨装,拥衾被半卧于榻上。隔着主尊佛像,与之相对的另一侧为半跏佛像,有观点认为此像应为文殊,但从图像来看,此尊与文殊菩萨之身份并无关联,笔者认为缺乏认定其为文殊菩萨之证据。另一幅维摩诘位于一尊佛像右侧,同为菩萨装,榜题可见“维摩诘之像”。关于炳灵寺《维摩诘经》题材作品,笔者更认同石松日奈子的观点,她认为炳灵寺石窟当中的维摩诘像缺少对应的文殊菩萨,而且维摩诘为菩萨装,未持塵尾,图像极为特殊。现存身份明确的文殊菩萨像,最早见于云冈石窟第7窟与第6窟,以第7窟之作品为最早,宿白先生认为第7窟开凿于魏孝文帝初期,长广敏雄先生认为第7窟开凿于470—480年之间。而第6窟则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公元494年迁都之前不久。这两窟中都保存有维摩诘与文殊对坐说法之浮雕。第7窟主室的维摩诘、文殊像风化较为严重(图1),但能分辨出文殊菩萨半跏坐姿,头戴冠,上身披帔帛,戴项圈、手镯、臂钏等饰物,微笑的面庞侧向身体右侧,左手拇指与食指捏持一椭圆形物,右手举于胸前,似握持一个小的花苞。第6窟的文殊像保存状态良好,头戴花草形装饰的三叶冠,上身着交叉于胸前的帔帛,下着裙,坐于矮榻上,左臂自然垂下置于左腿,右手于胸前手心向外半握拳状,似乎正与头戴尖帽,身着对领长衣的维摩诘高谈阔论。从外形特征来看,文殊之形象与当时的其他菩萨像并无差异,若不是与维摩诘同时出现,无法单从外貌和衣着特征来判断其身份。河北易县出土了和平六年(465)铭的交脚菩萨残像,金申先生在《易县北魏交脚菩萨像造型上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详细分析了这尊造像的风格特点与来源。此像正面残存菩萨腹部与双腿,背面有《维摩诘经》内容之线刻,为维摩诘与文殊对坐说法出现在单尊造像当中最早的实例。背面右侧屋形龛中,头戴花冠的人物形象应为文殊菩萨,于屏风前跪坐,双手握拳状举于胸前,身着宽袍大袖交领袍服,与左侧站立的四位听法天人装束相同。这尊像发现于河北易县,考虑到石质作品搬移不易,多为本地或出土地周边制作,因此这尊交脚菩萨像很有可能制作于易县或周边地区。台北故宫藏北魏太和元年(477)佛坐像,是现存最早出现文殊与维摩诘说法题材的金铜像,像的背面遍刻内容丰富的图案。顶端是坐在宝塔之中的释迦与多宝佛,画面中央为右手举起的佛陀说法像,文殊与维摩诘位于二佛并坐偏下的左右两侧,佛像左侧(即画面右侧)为文殊(图2),头戴花冠,袒上身,披帔帛,结跏趺坐,左手置腿上,右手举于胸前持如意。除持物之外,文殊与画面中其他菩萨像并无差异。人物躯体饱满健硕,与北魏公元500年之前流行之风格相符。这尊像铭文中提到的“安熹县”,位于河北定州东部,因此这尊金铜像很可能制作于河北。公元500年之后的造像中,文殊与维摩诘对坐说法之题材大量出现,尤以河南地区最盛,河南博物院藏北魏公元525年铭的弥勒造像碑中,文殊与维摩诘位于主尊弥勒菩萨的左右上方,文殊身着宽袍大袖的汉式服装,头梳高发髻,右手握L形如意(图3)。类似的例子同样见于河南东魏武定元年(543)所造的道俗九十人造像碑,以及河南浚县出土的北齐武平三年(572)佛时寺造像碑等作品。山西最为典型的北朝文殊像之一莫过于天龙山东魏时期(534—550年)的雕刻。现存哈佛大学博物馆的两件浮雕,原属天龙山第2窟与第3窟,其中的文殊菩萨同为结跏趺坐姿,坐于带有壸门的矮榻,面容清癯,一手于胸前横持外形似烟斗的L形如意,身着飘逸多褶的衣裙,是北朝佛教美术浅浮雕中的佳作(图4)。天龙山第三窟浮雕文殊菩萨,哈佛大学博物馆藏
现藏西安博物院的比丘法和造像碑雕凿于西魏大统三年(537),文殊与维摩诘说法像位于石刻作品的最上段,画面左侧的文殊呈跪坐姿态,左手自然下垂,似有椭圆形持物,右手举于胸前,掌心向外。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李阿昌造像碑为隋开皇元年(581)作品,出土于泾川县,造像碑正面内容分为四段,维摩诘与文殊之题材位于最下,右侧的文殊由于风化及损伤,局部不甚清晰,可见其坐于高台上,左手似置于腿上,右手举起,于胸前持略呈L形的如意。北朝至隋代,单体造像碑与石窟当中均有大量维摩诘与文殊说法之题材的作品,此处不一一赘述,其中的文殊,呈跏趺坐或半跏坐,手中持物多见如意,也有的文殊像手中无持物。如意为中国本土之器物,即古之“爪杖”,将爪杖称为如意,最早见于三国时期的记载。如意不仅是实用的瘙痒器具,也被作为一种宝物,受到上层人士的喜爱。在3—9世纪的文献和图像记载中,如意常常作为政治与军事人物、善于清谈的知识分子、高人隐士,以及高僧手中的握持之物。例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墓画像砖当中手持如意耍弄的王戎,历代帝王图中双手抚如意的陈文帝,均可说明此时如意之功用。印度佛教中也有僧侣使用的“阿那律”,其功能同样是用来搔背,汉文也将之翻译为如意。日本临济宗高僧无著道忠(1653—1744)在《禅林象器笺》“如意”条目中引述《释氏要览》对于如意之释文并称:忠曰:如意之制,心之表也,如此方篆書心字。此义不通印度焉。又曰:文殊岂欲搔痒也,是亦不然。世尊尚示有圊便疾病,既同凡受五蕴色身。何无复背痒耶。余窃谓,凡佛菩萨所执器物,动有所表。盖说法到人疑处,令彼能通晓,猶如爪杖搔痒处痛快,故执此表其相。若复依此义,则文殊虽执,亦何妨焉。此处从佛教角度解释了文殊所持之如意,认为如意是用来表法的,象征解疑答惑,如搔到痒处之痛快,是后世对于文殊持如意之象征含义的解释和理解。无论当初如意被作为文殊之持物是何含意,不可否认这种物品在当时上流社会和高人隐士之中的流行。与维摩诘对坐说法之文殊出现于北朝,手持如意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早期的如意实物少有存世,在日本正仓院的藏品中,可见唐代的如意,侧面呈非常简洁的L形,与北朝文殊之持物类似。如意作为持物,从未见于印度造像,这也说明汉传佛教中北朝的文殊像,确实为彻头彻尾的中国式形象,充满着汉文化对一位能言善辩、才思敏捷的菩萨之想象。汉传佛教中的文殊像,在出现伊始并非礼拜的主要对象,也不是佛龛中的主尊,而是常常出现在主尊周边,与维摩诘一起构成对坐说法之内容,提示了《维摩诘经》之流行,作为佛教故事装点背景。这一题材在佛教造像当中流行于北朝,少见于唐代。原因之一,大概是由于造像形制的变化。北朝多见大型造像碑,内容丰富,需要多种佛教故事或场景作为装饰,而唐代盛行单体雕塑,不需要过多的背景和故事作为陪衬。尽管维摩诘与文殊之形象少见于唐代造像,但并不能说明这一题材在中原消失了,少见的很大原因是由于唐代中原地区的大量绘画真迹未能留存下来。在《历代名画记》中,提到唐代长安的荐福寺与安国寺,有吴道子绘制的“维摩诘本行变”与“维摩变”,尽管无法知晓绘画的具体内容,但根据同时期与之前北朝的佛教美术状况,“维摩变”中出现维摩诘与文殊对坐的可能性极高。在敦煌莫高窟,维摩诘与文殊对坐法说之题材从西魏前后开始出现,至隋末唐初,维摩诘变相的绘制走向成熟,其内容丰富,场面宏大,华丽的构图与盛大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唐代至五代的敦煌绘制了大量宏幅巨制的经变画,装点着宽广的石窟内壁,维摩诘经变作为其中一种,流行于此实为情理之中。其次,文殊与维摩诘之形象与题材,最早并不流行于西域,而是集中出现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区域,这种汉传佛教独创的图像,从中原至敦煌,传播上有时间差,这或许也是敦煌在中原之后才盛行文殊与维摩诘题材的原因之一。二、唐至五代的汉传佛教文殊像9世纪前后,印度佛教美术中开始出现文殊像,并随着佛教逐渐传入汉地。印度文殊开始大量出现的时代,密教已然盛行,尽管早期的印度文殊像不一定和密教有关,但印度文殊像传入中国,却伴随着浓墨重彩的密教背景。唐以前的汉传佛教文殊像中,没有出现过优钵罗花或是宝剑、经书之类的持物,然而作为佛教正统的印度出现文殊像并影响到汉传佛教之后,唐代的文殊开始呈现多变的样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并行的图像系统。一方面是传统的延续,汉式持如意的文殊像依然流行,而且伴随着五台山信仰的成熟,具有稳固的地位并形成新的组合。另一方面是受到印度影响的文殊像逐渐传入中原,并与汉地传统相互融合。此外,汉传佛教中单独被供奉的文殊,也是从唐代才开始出现。唐代的汉传佛教美术中,维摩诘经变依然在流行,且形成了更加宏大的场景和复杂的构图,敦煌壁画是其最好的明证与实例。其中的文殊像,保持着早期汉式特征,大多手持如意,装束与其他菩萨无异。敦煌壁画出版物众多,研究著述宏富,关于唐代的维摩诘经变绘画,此处无需赘言。此外,唐代出现的文殊当中,常见的还有骑狮文殊,关于这一形象的来源,孙晓岗先生进行过详尽的论述。狮子最初常被雕凿或绘制在佛陀台座上,之后也偶见于主尊两侧胁侍菩萨的台座下方,例如西安文物管理所藏始光三年(426)三尊像及藏于四川省博的梁普通四年(523)等造像中,均可见两侧胁侍菩萨立于狮子之上。狮子既能装点于主尊台座两边,又能抬高两胁侍菩萨所处的位置,在构图上有一举两得之功,但狮子与胁侍菩萨之身份并无特定关联。大约在北齐时期,狮子被固定为文殊菩萨的坐骑。这时的印度,尚未出现骑狮的文殊,因此这一形象,并非来自印度的影响。初唐的敦煌,出现骑狮文殊与骑象普贤对称分布的构图,如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的药师佛净土变,第331窟东壁的法华经变,都有骑狮文殊与骑象普贤对称分布,随后又逐渐演变出牵狮驭象的随从等等更加丰富的组合形式。骑狮的文殊像,在唐代也常见于华严三圣题材。骑狮的唐代文殊像中,最值得关注的当属“新样文殊”。新样文殊之称呼,见于敦煌莫高窟第220窟骑狮文殊像题记中所说“敬画新样大圣文殊师利菩萨一躯”,根据这篇题记,可知此为翟奉达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施绘。关于新样文殊,已有诸多研究成果,此处不再赘述。简而言之,所谓新样文殊,是由文殊为中心构成的一组人物,不与骑象的普贤菩萨对称出现。在“新样文殊”中,文殊菩萨骑狮,驭狮者由昆仑奴的形象变为于阗国王。新样文殊与五台山信仰关系密切,并随着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兴盛流传到各地。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代版画中,有刻印“大圣文殊师利菩萨”(图5)的作品。主尊文殊为正面像,头戴宝冠,手持如意,左腿垂下,半跏趺之姿态骑于威武的狮子背上,右侧有双手合十,谦卑恭谨的善财童子,左侧是深目高鼻,穿袍着靴的于阗王形象,下方文字称“此五台山中文殊师利大圣真仪”。这种图像与五台山关系密切,并传入日本。北宋入五台山巡礼的日本僧人奝然,从中国请回的物品中,包括藏于日本清凉寺释迦像内的骑狮文殊与骑象普贤版画,其中的文殊像即为此种形式。除了这种文殊三尊像,也出现了五尊形式,即增加了由“文殊化老人”故事而来的佛陀波利和老人像,构成文殊菩萨、佛陀波利、善财童子、大圣老人、于阗国王这五尊的组合。文殊菩萨版画,大英博物馆藏
无论是与骑象普贤对称出现的骑狮文殊,还是新样文殊,就文殊像本身来说,手持如意的骑狮形象,继承了汉传佛教文殊像的传统。骑狮的文殊像在印度也有,但出现晚于汉传佛教造像,不排除唐代的文殊骑狮像或许也曾受到印度佛教美术的影响,外来因素加之本土的传统,骑狮的文殊像出现在唐代并不奇怪。除了北朝以来的汉式文殊,唐代的文殊像出现了新的变化。安国寺位于唐长安城的长乐坊,是唐代的皇家寺院,为睿宗舍旧宅而成,从安国两字能够窥见寺院的主要功能和目的。安国寺遗址出土了几件白石造像,其中有一尊雕琢精美的文殊像(图6)。造像表现出典型的唐代面貌,文殊菩萨面部饱满圆润,眉毛弯而长,细长的双眼呈俯视姿态,鼻尖有损伤,小巧饱满的口唇呈起伏的波浪线,为唐代佛教造像的特征。文殊双腿结跏趺坐,双手抬起置于胸前,左手持优钵罗花茎,花朵开放于左侧肩头后侧,花上载有经书,右手残缺。这尊文殊菩萨像的持物,并非汉地常见的如意,显然是受到印度影响之后出现的形式。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帛画中,有一幅文殊画像(图7)。文殊身着透明轻纱裁成的帔帛与下装,半跏趺坐于狮背的莲座上,小巧的五叶宝冠,额前及肩上黑色的小卷发,明显具有印度波罗王朝之特色。文殊左手所持的优钵罗花,常见于印度文殊像。单从这尊文殊的图像学特征来看,持物和印度文殊像类似,装束也非汉地特征,虽不知这幅画作是否直接参考了印度的图像,但一定是印度文殊像辐射周边的结果。尽管这幅文殊像本身属印度系统,然而文殊莲座下的狮子与昆仑奴则吸收了汉传佛教美术传统。敦煌地处东西交通要塞,其绘画也常常具有东西融汇之画风,在这幅作品中得到明确的体现。文殊菩萨像,大英博物馆藏
另一幅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佛八大菩萨绘画中,也有文殊之形象。这幅画作的部分尊神旁边写有藏文榜题,推测为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绘制的作品。文殊菩萨位于主尊右侧(画面左侧)第三位,面容及衣着皆为唐风,双腿散盘,右手置于右膝,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左手于胸前持经箧,并非汉式特色。一佛八大菩萨的组合来源于印度,埃罗拉石窟当中就保存着多处9世纪前后的浮雕作品。这幅作品中的文殊明显受到印度图像的影响,手持经箧的文殊像在这一时期的汉地并不常见。我们并不清楚唐代的汉地究竟存在过何种文殊像,许多实物资料如今早已遗失或损坏,但是从日本僧侣请回和整理的唐代图像中能够管窥当时之状况。印度的文殊像未必一定和密教相关,但文殊像在印度形成之时,密教已然开始流行,因此文殊像是伴随着密教背景传入中国的。这些图像随着唐密传入日本,一些资料在日本被保存至今,比如《胎藏图像》,为唐代密教美术图像集之一,卷尾绘制了手持莲花、行炉与念珠的善无畏三藏白描像,旁有墨书“中天竺国那兰陀寺三藏法师善无畏于大唐东都河南府大圣善寺译出”,善无畏出生于东印度,开元四年赴长安,开元十二年入洛阳,为开元三大士之首。根据墨书记载,可知《胎藏图像》由唐代洛阳的善无畏传承而来。其中描绘的一尊文殊菩萨左手持优钵罗花,半跏坐姿,虽然此优钵罗花与印度有所不同,但明显不同于观音所持之莲花,花瓣收束,应为印度一系图像而来。另有一幅曼殊室利童子像,头上有三髻,胸前颈饰垂挂的方形与圆形饰物与印度文殊像如出一辙。文殊童子左手持花瓣尖细的优钵罗花,其上有金刚杵,正如大日经中所说“左持青莲花,上表金刚印”。这些文殊像明显具有印度特色,并曾在唐代传播。正如孙晓岗先生所说,相比汉传佛教来说,日本佛教美术中的文殊像,更多具有密教色彩,比如五髻文殊、童子文殊等。但我们不能忽略,这些图像是从中国传入了日本,只是并未在汉传佛教中保留至今或者形成普遍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汉传佛教中的文殊像比印度形成要早,在印度图像传入之前已然形成了完全中国化的图像,并随着五台山信仰的兴盛,被固定和传播开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印度式样文殊像的流行和制作。第二,唐密在中国大多限于社会上层,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并未成为民间佛教信仰的主流,因此唐密图像没有普及到民间也是情理之中。唐代的密教经典中,还记载了千手千钵文殊,其图像见于敦煌壁画。这种文殊像较为特殊,也有一些研究成果公诸于世,有人认为不空所译《大乘瑜伽金刚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钵大教王经》是千手千钵文殊图像的依据,也有人认为此乃一部伪经,千手千钵文殊像是依据其他经典,并杂糅了五台山信仰改造而成。千手千钵文殊不见于印度,其来源等问题还有待更多的研究,因此作为一个特例,不在本文中进行探讨。到了西夏与元代,传统的汉式文殊在五台山等地依然被继承和保存,但与此同时,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和兴盛,藏传佛教图像开始逐渐流行于内地。藏传佛教文殊像承袭了印度传统,并形成了一些自身的特色,这是另外一个大的系统,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主题,暂不讨论。结语汉传佛教美术中的许多图像具有强烈的本土特征,文殊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证。文殊之名及相关经典毋庸置疑来自印度,但是其尊像在汉传佛教当中,从出现伊始就是中国化的形象,而不是印度佛教图像影响之下的产物。现存的印度佛教美术实物当中,9世纪前后才出现明确的文殊像,但不能否认之前的时代可能早已有文殊之形像,只是未留存至今。即便这一假设成立,中国北朝的文殊像,无论是作为持物的如意,还是宽袍大袖的汉式服装,均非印度特色,文殊菩萨与维摩诘一同构成故事场景,常出现在主尊上方左右。这一图像伴随着《维摩诘经》的普及在中原地区最为流行,并演变成为复杂的构图与场景,在隋唐时期的绘画中展现出宏大的篇章。随着佛教美术的发展,骑狮的文殊与骑象的普贤开始对称出现,大约在北齐时期,狮子固定成为文殊菩萨的坐骑。骑狮的文殊像,在唐代伴随着五台山信仰的发展与兴盛,成为单独被供奉的对象,最终形成“新样文殊”流传各地。印度佛教在9世纪前后出现了文殊像,并随着佛教,尤其是密教的传播对汉文化产生影响,汉地的文殊像开始逐渐加入印度元素。在唐代的中心长安,安国寺白石像中出现印度式样的文殊。在流传东瀛的图像集中,依然保存着善无畏于唐代洛阳传授的图像,其中的文殊同样呈现印度特色。而位于东西交流要塞的敦煌,则保留着中印特征混合的文殊像。回顾汉传佛教文殊的图像特点及其发展历程,充斥着创造与传承,及文化碰撞带来的变革,这一进程,与印度文殊像出现的时间和发展轨迹不谋而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印度的文殊像出现之前,汉传佛教中已经创造出中国化的文殊形象,表现出中国佛教美术极具创造性的一面。随着《维摩诘经》的流行,汉传佛教并非在被动等待图像的传入,而是根据经典内容创造出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场景。在印度的文殊像传入中土之后,又善于吸收外来因素和文化,从而在历史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佛教美术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