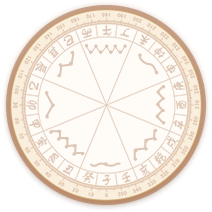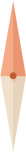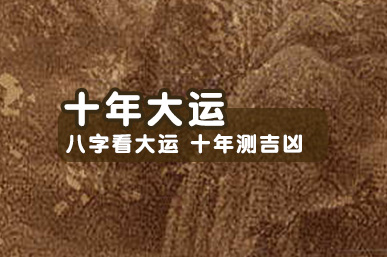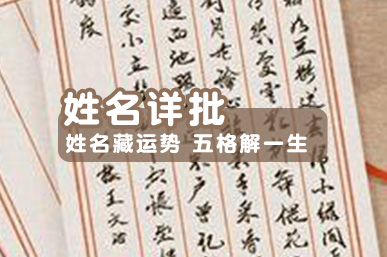漫谈八字之流年
流年亦称太岁,岁柱。是八字命局所经历的某一年份,由岁干和岁支组成,其干支阴阳五行属性,与特定人八字、大运形成生克制化关系,从而决定了这个人在本年度中运气好坏。
流年对命局是一种外在约束力,是宇宙大自然力量,是一种不可抗拒和改变的力量。它可以左右命局,只是因为命局组合不同,其应变能力不同,则结果好坏与吉凶程度不一样。
一般情况下,太岁是不可冒犯的。古有太岁当年坐,冒犯必有祸之说。太岁是皇帝,是当年的天子,是众生之主,主一年生杀大权。太岁的原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冒犯了太岁,轻者为祸百端,重者有杀身之灾。
太岁克我,为上克下,皇帝统治天下臣民,父亲管教儿子,上级命令下级,顺理成章,即使不满,只要不反抗,不冒犯,则无灾或即使有灾也轻;我克太岁,为下犯上,如儿子打老子,臣民反皇帝,则为不孝,为犯上,龙颜必大怒,轻者受伤、疾病、破财,重者会有牢狱、杀头、丧命之祸;太岁生我,为上生下,天子体恤臣民,父亲慈爱子女,命主则平安康泰,喜事连连;我生太岁,臣民供养天子,子女孝顺父母,乃为人伦之道,命主必遵纪守法,恪守孝道,自然有后福。
流年相当于一辆车在某条道路上行驶的节点,好动流年,说明正在行驶的道路上节点畅通,路况良好;不好的流年,说明此道路节点是坑洼处,拐弯处,发生了交通事故,总之车辆是不能通畅的通行。
流年这种力量共有六十种,一年一变,按特定规律循环往复。对特定命局来讲,有时雪上加霜,有时雪中送炭,有时锦上添花,有时大煞风景;对不同的命局来说,有的命局为吉,有的命局为凶,而且吉凶程度也不一样。
这是我见过最无知的一句话,却被广泛传播,还成了流行语
古时候的强盗土匪常说一句话,叫“天是王大,我是王二”,就连古代土匪都有敬天畏天之心。可现在流行这么一句话,叫“我命由我不由天”,说出来好像显得自己多霸气、多有学识,殊不知其中充满了无知、任性。如果一个人连天都不知敬畏,还妄自尊大,以人力而贪天功,其结果必至于《中庸》中所说的“小人而无忌惮”!难道现在的国人连古时候的土匪山贼都不如吗?!
中庸章句
我命由我不由天,不知道这句话出自何人之口,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的。现在有些人倡导弘扬传统文化,莫非以为这句话就是传统文化?把这句话当成传统文化来倡导?但其实这句无知的话跟传统文化没有半点关系,甚至是站在了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对立面上。
当然,古代不敬畏天命的人也有。比如那位北宋变法的王安石,便说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但他对这两句话的奉行结果是天下大乱,终至奸臣以绍述为名,而有靖康之难。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说,让人敬天畏天,为的是让人(包括皇帝)心里存个敬畏之心。就像孔子早就说过的那样:“敬神如神在。”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10月11日)
那么真正古代的正统的儒家是如何理解天命的呢?让我们从《中庸》的第一句话说起。
《中庸》开篇就说:天命之谓性。
这里的命字有两个意思:
一是,如朱子的解释,命犹令也,也就是命令的意思。命是由天发出的,天以此而生万物,如上使下,上层给下属发命令一样。至于天是如何命万物的,那是另一个问题,说起来就话长了,不宜在此多说。
二是,万物(包括我们人)体此命、受此命而为自己的生命运途,即是所谓的命运。
由此可见,我们人之人性,和万物之所以为万物,都是由天所命的,是从天发出来的。而我们人所承受的这个天之所命,也就是我们人的命运。由天所发,当然是至善无一毫之恶的,只要我们人顺着这个天命之性而行,也就会至善无恶,这就是《中庸》的第二句话:率性之谓道。
朱子像
但那就奇怪了,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承受此天命,都有此至善之性,那为什么会有坏人呢?另外,又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享福,而有的人又命途多舛呢?
我们每个人的性都是一样的,都是善的,但这个性只是个潜在的东西,它还得发出来才行。一旦这个性发出来,就会有个过与不及的危险。所以,有些人秉性纯一,发出来就和于此性,就能中节;而有些人难免有气质之偏,发出来或过或不及。但只要能循此天命之性而行,即使暂时过与不及也没关系,毕竟知此性才能知道哪是过、哪是不及。
可怕的是,有些人竟然不知道这个天命之性,这样也就没有个约束,所以必至于任性而行、无所不为、肆无忌惮。这就是所谓的小人。
那又为什么有人就能享福,而有人就受苦受罪呢?或说,为什么有的人命好,而有的人命不好呢?
这就涉及命的另一种二分,即理命和气命(详见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
牟宗三(1909年6月12日-1995年4月12日)
所谓的理命,就是上面所说的,我们每个人所秉受的天命之性。而所谓的气命,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不同境遇。为了说明二者的不同,我们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孟子,尽心下》中有这么一句话: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先说“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然后又说“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不是相互矛盾吗?当然不是,因为其中的两个性字和命字有着不一样的意思。
孟子像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这第一句中的“性也”是小人说的,他说:嘴里要吃好吃的,眼睛要看好看的,耳朵要听好听的,鼻子要闻好闻的,胳膊腿儿都要舒服,这都是人的天性。所以追求这些都不为过。这个小人所说的性并非是天命之性,不是超越的性,而是实然的性,所谓性者生也。
但是君子反驳道: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这个命字就是理命。君子的意思是说,虽然口目耳鼻四肢都追求好的、要舒服,这是人的本性,但是有天命在,所以人应该顺此天命,而不应该只满足于肉体的欲望。
《孟子正义》
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第二句中的命字则是小人说的,是气命,而不是上面君子所说的理命。小人说:说什么仁义礼智圣,我们每个人的命遇都不同,有人富贵,有人贫贱,所以我不能做到仁义等德行,这也不能怪我,这都是命运使然。
但君子反驳道: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这个性字则是超越的性,而不是上面小人所说的实然之性。君子的意思是,仁义礼智圣这些都是天命给我的人性,我们人要遵循此德性,不能因为命运不好就放弃。
由此可见,虽然命字有气命一说,人有富贵贫穷的命遇不同。但即使是这种气命,我们也不能与之抗争,因为你抗争了也没有用,所谓的求之不在我者也。但这也不是说听天由命、无所作为了,而是要努力地遵循天命之性,修此仁义之德性,所谓修身、求之在我者也,求则得之。
所以,我们不要求命、抗命,而要修身已俟命,这样才是君子之所为,而不要行险而邀幸,这是小人。就像张横渠所说的那样:生吾顺事,没吾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