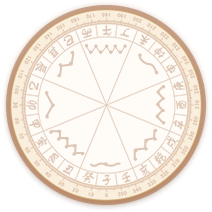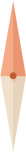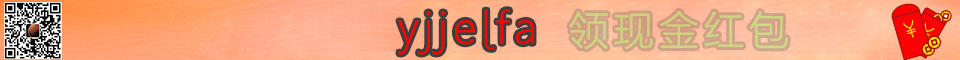

本文目录一览:
孔劳格评《爱与友谊》︱用爱的书单拯救爱
在一个充斥着诡辩家、卫道士、浮夸专家的年代,布鲁姆是一位老师。
——阿兰·布鲁姆的学生、共和党军师威廉·克里斯托
阿兰·布鲁姆:《爱与友谊》
爱的书单
在《爱与友谊》里,阿兰·布鲁姆开篇以《爱欲的堕落》点题之后,第一部分讨论卢梭,以及受其影响的浪漫派作家,解读的作品包括卢梭的《爱弥儿》、《新爱洛伊丝》、司汤达的《红与黑》、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二部分将视线移至现代与古典的联结——莎士比亚,讲解莎士比亚几部以“爱欲”为主题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一报还一报》《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冬天的故事》。随后,以论述“友谊”主题的篇章——一篇讨论莎士比亚的《哈尔和福斯塔夫》,另一篇讨论蒙田和拉博埃西作为过渡。最后一部分解读希腊哲人柏拉图论述爱欲的名篇《会饮》。(中译本基本遵照英文原版,将三部分拆成三卷出版。唯一一处改动是:讨论《哈尔和福斯塔夫》的文章,被并入讲解莎士比亚的第二卷,而讨论蒙田和拉博埃西的文章则被收录到第一卷。)
可以说,布鲁姆在《爱与友谊》中,将作者、书目作为讨论单元,运用平易近人的行文,在向读者做一件老师经常做的事情:开书单。就像美国知识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布鲁姆——哈罗德·布鲁姆撰写《西方正典》一样,我们不妨把《爱与友谊》视作是为“那些仍然觉得经典著作很有吸引力的人、以及那些对爱情描写有着长久兴趣”的读者,献上的一份经典著作的书单。
《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
《爱的戏剧——莎士比亚与自然》
《爱的阶梯——柏拉图的〈会饮〉》
布鲁姆曾不无痛惜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一本经典著作或一位伟大作者的反复阅读与信赖逐渐消失,这将导致生活基调的庸俗化和社会的原子化,也将瓦解一个社会对善恶尊卑的基本共识。这样的基本共识离不开柏拉图、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伟大作者的经典著作。布鲁姆写作《爱与友谊》,隐含着这么一个期待:通过这些经典著作,帮助迷失的现代人,重返爱的教育。
对于传统上就强调礼教的中国,布鲁姆书写《爱与友谊》的启示,恐怕正在于让我们看到爱的教育与经典作品阅读之间的关联。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教养资源,来帮助我们理解“爱与友谊”这一亘古通今的主题。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我们对“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一疑问,又有哪些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比如布鲁姆在本书中所着重讨论的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的理路?
论战余波
自从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开始,布鲁姆被引入中文学界已有二十余年。对布鲁姆比较熟悉的中国读者,大概不会把《爱与友谊》仅仅当成一份书单。这本布鲁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与他之前的著述和思考,息息相关。
阿兰·布鲁姆
布鲁姆1930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的祖父母从欧洲移民到美国费城,是一对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的父亲在犹太慈善机构工作,母亲是社工。布鲁姆年少时,随家人从印第安纳州迁居芝加哥,十五岁即被哈钦斯校长治下的芝加哥大学录取。在余下的漫长岁月里,布鲁姆的生活轨迹再未离开大学校园。他仅仅花了三年就完成本科学业,随后留校攻读社会思想委员会研究生。博士毕业,布鲁姆先后在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授课。1960年代美国学运声势高涨,三十多岁的布鲁姆因不满康奈尔校方纵容学生、懦弱无为的表现,愤而离职。之后,布鲁姆在巴黎和海德堡游学,又辗转多伦多大学任教数年。1979年,布鲁姆回到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直至1992年逝世。
作为施特劳斯的得意门生,布鲁姆运用其施特劳斯学派解经注经的技艺,翻译和注释了柏拉图的《王制》(1968)、卢梭的《致达朗贝尔论剧院的信》(1960)和《爱弥尔》(1979),这些译本均位居这些著作的权威英译本之列。早年,布鲁姆与师兄哈瑞·雅法合著了《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64),到八十年代,他本人先后编著了《美国和自由教育的危机》《美国精神的封闭》《直面宪法》《巨人与侏儒》。病逝前,布鲁姆写下了《爱与友谊》。
布鲁姆在美国知识界声名鹊起,无疑有赖于其1987年出版的《美国精神的封闭》。该书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鲁姆的同事兼好友索尔·贝娄作序,直戳时代大学教育的痛处,引发的辩论震撼当时的美国知识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美国大学教育的讨论中感受到论战的余波。布鲁姆也因此一战成名,陷入舆论的漩涡:里根总统白宫接见,电视电台接连采访,报刊杂志争相报道……
心直口快的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如此描绘美国大学的爱欲图景:
要想进入今天大学生的世界,最佳途径就是看看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在曾经被称为“爱”的事情上,他们通常不会说“我爱你”,绝对不说“我永远爱你”。一个学生对我说,他当然对女友说过“我爱你”,那是“在我们分手的时候”。这种分手干净利落——互不相伤,都无过错,他们精于此道。他们把这理解成道德,理解成对他人自由的尊重。也许,年轻人是出于诚实才不说“我爱你”,他们体验不到爱——他们太熟悉了,以至于把和爱混为一谈了;他们只顾自己的命运,以致无法为了疯狂忘我的爱而做出牺牲……青年男女拥有的是“关系”(relationship),而不是“爱”……“关系”需要靠双方去维持,而“爱”则能够自发生长。在“关系”中,双方首先想到的是麻烦,所以得去寻找共同的基础。“爱”则通过想象力呈现完美的幻觉,把双方交往中的分歧抛之脑后……有很多大学生是两人同居,他们自称“室友”,房租中既包含水电费,也包含性行为……想通过古典文学了解自身状况的学生就更少了,古典文学从伊甸园起就把描述成极为隐秘和复杂的事情。今天的大学生左思右想也搞不明白,如此煞有介事是为了什么。(摘自《美国精神的封闭》,2007,译文稍有改动)
《美国精神的封闭》
玛莎·努斯鲍姆在她著名的批评文章里指出,布鲁姆在书中讨论的学生,属于少数精英学校的天之骄子,根本不能代表大学生群体,不但以偏概全,更是精英主义的表现(Martha C. Nussbaum, Undemocratic Vistas: Review of Allan Bloom, 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40-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然而,二十年多来的事实证明,布鲁姆的这些观察并非像努斯鲍姆批评的那般有失公允。现如今,美国大学的爱欲图景比起布鲁姆三十年前的描述,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Open relationship”“friends with benefit”“one night stand”和“short time relationship”这类代表着“有性无爱”生活方式的词汇,或许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稍显刺耳,却已在当下的美国大学里不足为奇。
布鲁姆在《爱与友谊》中引入对古典爱欲的推崇,可以看成其《巨人与侏儒》的“古今之争”主题在“爱欲”领域的进一步展开。当然,《爱与友谊》更直接回应的,是《美国精神的封闭》里描绘的美国大学爱欲图景。如果我把《美国精神的封闭》比作对美国大学爱欲图景的诊断册,那么《爱与友谊》就是布鲁姆对此病症开出的药方。
爱的探究:浪漫主义的努力
《爱与友谊》开篇直奔主题。在题为“爱欲的堕落”的导言中,布鲁姆一边对《美国精神的封闭》所遗留的问题展开回应,一边以倒叙的形式,步步为营,为整本书搭建脉络、定下基调。在布鲁姆看来,“爱与友谊”在现代社会最大的威胁,便是抛弃道德观念的相对主义和主张权利斗争的女性主义。
布鲁姆首先回应了两位现代科学主义的代表:金赛和弗洛依德。在布鲁姆看来,虽然这两位科学家在讨论性和爱时智识高低不一,但却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摒弃了善恶正邪的道德观念。于是,两人殊途同归,陷入相对主义泥沼。接下来,对于将爱简单抽象成男性和女性权力斗争的激进女性主义,布鲁姆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凡此种种的歪曲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将爱——一种建立在自然的甜蜜、相互关心,以及对共同的孩子的永恒关注之上的东西——变成一种权力斗争。”
回应文化论战之后,布鲁姆笔锋一转,用施特劳斯学派擅长的方式,“试着去发现真正的爱欲”——布鲁姆带领读者阅读几位论述爱与友谊的经典作家:卢梭、司汤达、奥斯丁、福楼拜、托尔斯泰、蒙田、莎士比亚和柏拉图。
布鲁姆译《爱弥儿》
第一位进入读者视野的,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卢梭。布鲁姆对卢梭的热爱有目共睹:他早年就翻译卢梭,而在施特劳斯学派的经典政治哲学教材中,也亲自撰写了卢梭一章。这一次,在《爱与友谊》中,布鲁姆把近四分之一的篇幅献给了卢梭。在他看来,卢梭的爱情观试图将从教的原罪当中拯救出来,融合最纯洁的精神渴望和最完美的肉体满足,重构现代人的爱欲。在卢梭及其浪漫主义门徒的爱情小说中,这种具有深厚基底的爱情观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于连和玛蒂尔德的爱,比之于连和德·雷纳夫人的爱,哪一个更崇高?什么样的婚姻才是最理想(或者最糟糕)的婚姻,是维克翰和莉迪亚,夏洛特和柯林斯,简和宾利,还是伊丽莎白和达西?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局,谁更值得同情?布鲁姆引领读者们接近这些有关爱的问题,并通过其解读带给读者更清明的认识。
对卢梭及其浪漫主义门徒,中国读者应该比较有亲和感。因为一方面这些作品与现代社会在时空和文化上十分亲近,另一方面,卢梭是立足于婚姻和家庭来试图解决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人的问题的,这两者都是儒家传统极为关切、而本书后文强调的希腊传统相对淡化的问题。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英国作家奥斯丁的作品里,表现地更为生动具体。
在讨论婚姻和家庭时,奥斯丁融入了对自爱(amour-propre)和虚荣(vanity)的讨论。在奥斯丁看来,如果一个人可以随便和多个伴侣发泄,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力量去追逐崇高的爱。她笔下的伊丽莎白蔑视这样的人,对她而言,只有包含着对爱的最高渴望时,才是重要的。同时,奥斯丁认为,婚姻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真爱,而不是理性算计或虚荣势利的基础上。“再没有比包办的婚姻更背离奥斯丁的精神了。”这一十足的浪漫派情怀,在奥斯丁的多部小说里——尤其是《曼斯菲尔德庄园》——均有体现。然而,奥斯丁对节制这一古老德性的坚持(尤其是她对通奸行为的反对),似乎让人看到了布鲁姆开篇所引用的、批判卢梭浪漫主义的英国思想家艾德蒙·柏克的影子。因此,奥斯丁便带有了几分古典色彩,与卢梭及其他几位浪漫派作家拉开了距离。
反观卢梭这一更为彻底的浪漫派,他为恢复爱欲所做的努力,在布鲁姆看来,注定要失败。卢梭的浪漫主义也许可以帮助消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但这并不足以在现代社会恢复“爱欲”本身。书中的这段话或许是对一失败所作的最好的注解:
因为卢梭和他的门徒们试图无中生有,试图用一根绳索将人从最初的泥淖里拉出来,但这根绳索却无法和任何位于高处的东西相连,除了希望和抱负。歌德用一句话道出了这种浪漫主义信仰:“那个永恒的女人(The Eternal-Feminine)引诱着我们向上。”尼采嘲笑了这句话。弗洛伊德和金赛正在花园小径的尽头等着。(第一卷,59页)
爱的探究:回归柏拉图
在这番悲观论调之下,布鲁姆在第二卷引领我们来到莎士比亚的世界寻找答案。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与卢梭和他的浪漫派信徒截然不同,他并没有尝试去重构现代人的爱欲,而是“尽力恢复爱欲最自然的样态”。布鲁姆注意到,在当时西方社会,法国的拉辛和莫里哀、德国的莱辛和歌德、意大利的但丁和彼得拉克纷纷丧失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而莎士比亚或许是唯一一位仍受欢迎的古典作家。时至今日,伦敦的莎士比亚剧场依旧火爆,莎士比亚戏剧在全球各地长演不衰,近现代的诗人、小说家、导演、画家等,也不断汲取莎士比亚的养分。这样看来,莎士比亚几乎是现代人与古典的唯一联结。
莎士比亚描写爱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以及对克服哪怕是死亡的希望。与此同时,莎士比亚也向读者展现了爱的盲目和缺憾。在他的笔下,美德与理性的地位高于;与之相对,浪漫派偏爱,意欲将其置于美德与理性之上。正是遵循这样的古典理念,莎士比亚对爱不吝赞美,但他也提醒读者,爱不是生活的全部,它需要与家庭、宗教和政治的要求达成妥协。正是在古典自然理念的指引下,莎士比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审视爱与友谊这一主题。
在进入最后的柏拉图篇章之前,布鲁姆用两篇以友谊为主题的文章过渡:第一篇写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尔和福斯塔夫,讨论地位差异的师生/君臣之谊;第二篇写蒙田和拉博埃西,讨论地位平等的手足之情。在蒙田那里,友谊是超越家庭礼俗的、完全自由的选择,建立在哲学之上。这一点和希腊人相通,因为在布鲁姆看来,希腊人不但是哲学的源头,也恰恰是友谊的源头。于是,以蒙田的《论友谊》作为铺垫,布鲁姆将我们引到七八位雅典精英讨论爱欲的思辨——我们来到了柏拉图的《会饮》。
柏拉图的《会饮》
在布鲁姆看来,与《斐德若》对爱之狂迷的赞颂略有不同,柏拉图在《会饮》中“不但与莎士比亚一样忠于自然理念,而且他还通过一个比戏剧更宽的光谱来表述爱欲,并对爱欲的意义做了一番更为贴切的理性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布鲁姆在对《会饮》的诠释中,并没有像导言所批判的弗洛依德那样,执着于阿里斯托芬的发言(尽管他也认真地对待了这位在《云》里嘲讽苏格拉底的喜剧家),而是将更多笔墨用以解读苏格拉底爱神的故事、爱的阶梯(美的身体、美的灵魂和美本身),以及爱对人的意义。
与此同时,布鲁姆还将视野投向了为《会饮》所回避,却与爱欲关系密切的一个主题:家庭。出生于传统犹太家庭的布鲁姆,敏锐地抓住了希伯来传统与希腊传统在处理爱欲与家庭礼法关系上的分野。希伯来传统通过家庭,乃至上帝之爱,限制个体爱欲:“《圣经》教给我们一种强烈但受到严格限制的爱欲倾向,一种被人的堕落以及由此导致的违背上帝命令的行为所玷污了的爱欲。上帝的法谴责所有不顾家庭的行为,并且促进家庭的爱欲。”与希伯来传统相对,“以政治和思想自由为目标的希腊人,他们质疑家庭乃至法律。恰恰是那些与家庭和法律相冲突的欲望和渴求成为爱欲的核心,并反过来变成自由地发现自我的”。
这样的希腊传统也折射到《会饮》的文本——整部有关爱欲的对话几乎只字不提家庭(或许唯一能和家庭沾边的只有苏格拉底对爱神厄若斯家族的介绍)。希腊人在政治生活中是城邦的一员,在哲学生活中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家庭处于一个从属位置,这在柏拉图另一本著述《理想国》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此,希腊传统中的爱欲纽带,比起希伯来传统更为分散。作为这两个传统的后代,现代西方人对爱欲的理解饱含了二者的张力和混合。这在莎士比亚笔下的克里奥佩特拉与海丽娜、鲍西亚与朱丽叶的对比中,体现得惟妙惟肖。
在全书最后一节,布鲁姆再次回到现代爱欲问题的讨论。他点出了苏格拉底与尼采关于爱欲问题的不同理解:对于尼采,人的本质处境是孤独,而权力意志是超越爱的存在,所谓“向死而生”;对于苏格拉底,爱是灵魂对整全和不朽的渴望,所谓“向永恒而生”。布鲁姆诚恳而严肃地解读尼采,但最终还是倾向柏拉图的理路。
布鲁姆书写本书之时,冷战硝烟刚刚散尽,美国这一现代政体站上世界之巅。巧合的是,《会饮》所发生的年代,正是古代政体雅典的巅峰,《会饮》后不久,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失败,走向没落。而发起、领导、最终叛变西西里远征的,恰恰是《会饮》中晚宴的闯入者、错过苏格拉底爱欲教诲的阿尔喀比亚德。作为对现代时代爱欲堕落的回应,布鲁姆似乎也想通过本书引导现代人,回归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针对爱的教育。也许正是这种爱的教育,才能塑造城邦成员(包括统治者)的整全和不朽的灵魂,也正是这样整全和不朽的灵魂,才有可能阻止政体的堕落。
结语
《巨人与侏儒》
唐豪瑟在一篇追忆布鲁姆的文章中提到,布鲁姆希望像他的老师施特劳斯那样影响年轻学生(《巨人与侏儒》增订版,14页)。究竟怎么才算是影响年轻学生呢?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留下了这么一段率真的回答:
作为教师,最令我得意的事情之一是,我收到过以为极出色的学生在初访意大利时寄来的明信片,他写道:“你根本不是一位政治哲学教授,而是一个旅游中介。”这话再好不过地表达了我教书育人的意图。他认为我使他做了好观察的准备,所以他能对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亲自进行思考。佛罗伦萨真正令人激动的东西,其价值十倍于全部的思辨哲学定理,关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是可信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一定要努力从学生身上发现那些渴望完美的因素,并重构那些能使他们自愿寻求完美的学问。(《美国精神的封闭》,19页)
读者们不妨跟随这位称职的“旅游中介”,打开这份爱的书单,探究《爱与友谊》的奥妙。